
此次展览,包括钟颖所造之《佛像》系列和《我》系列。佛我之间由并置而生观照,作品用不同材质辅以镂空、铸造、甚至是和植物、土壤的嫁接来完成,从而显现以变化求平衡的过程,而这种平衡在作品间所呈现的便是一种“和气”,但它并非一团和气之气,而是一种由和谐、疏离和流变共同构成的玄思与氛围,这也成为展览中最动人心之处。

“如何用当代的艺术形式传达我对佛学智慧的体悟,并能去除佛像在很多人尤其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偶像崇拜的迷信色彩,使佛造像艺术与当代社会生活真正产生有益的关系是我做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三世佛》的坐像在静穆的背景之下排列,光影之间产生了由具象到抽象,由实体到虚空,以至“由形至意”的蜕变,这一过程的表象是佛教中的“佛”作为偶像存在的瓦解过程,其内在则是对固有成规与执迷的破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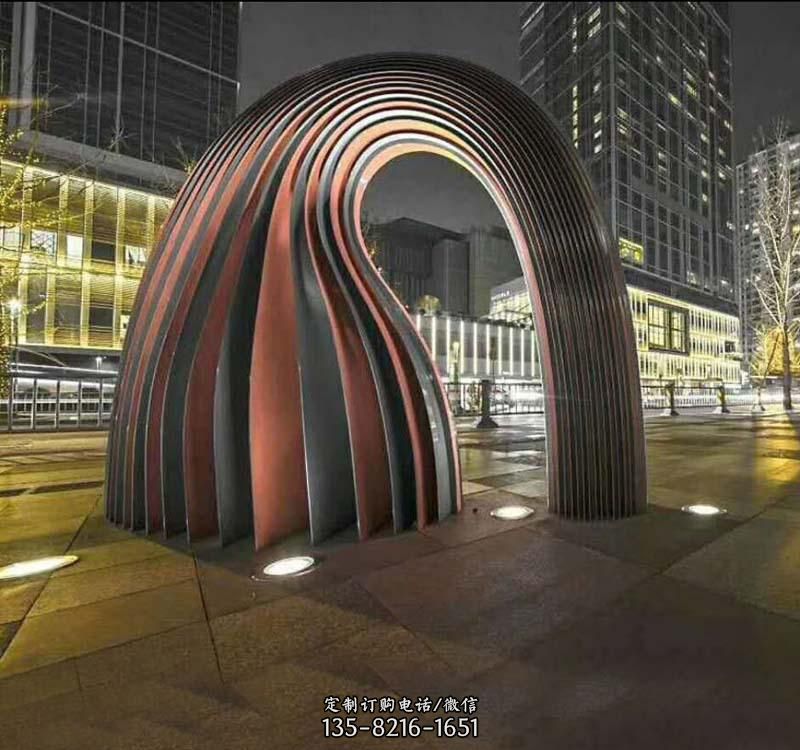
而最令我所感兴趣的却是,在这一破斥过程中,作者对所去除之形与所余下之像的主观选择,因为选择背后的不经意,往往便是真性情。而在另一件作品《佛陀》中,史钟颖对自我雕塑语言做了装置化的尝试,他在佛陀的形象与空间的虚实关系中,以“化身”之法展开,使观者在不同视角的观察过程中,困顿于形象与空间的边界,并由“像”生“意”,而模糊掉宗教与艺术本体间的界限,以至在这些许迷离之中,窥见“我”之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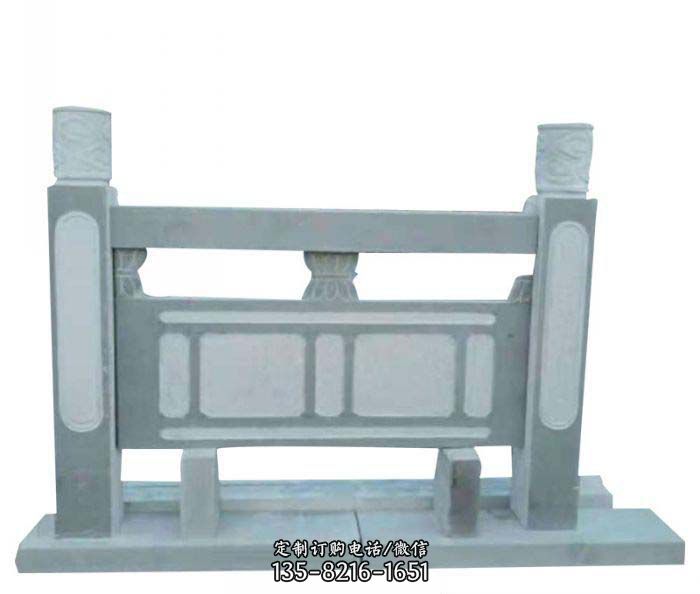
在史钟颖本次展览所使用的艺术语言中,佛教题材虽占据着绝对核心地位,但是观者却处处可见“我”之存在,尤其是《我》系列作品,皆以藏传佛教磕长头朝圣的典型人物姿态为蓝本,结合不同媒介而形成了对佛、对“我”问题的深入思考。“佛家对‘我’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我’并不仅指人的身体,更广义是指一切存在独立不变的主体自性,对‘我’执着的结果是不得解脱不得自由。

磕长头朝圣的行为本是藏传佛教中,放下傲慢完全放弃‘我执’的一种谦恭态度的体现,而非一般人对佛教误解的那样是对偶像的崇拜。但这组作品并未以通常着藏袍的形象去表现,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体为原形以强调切身的体验,并运用最根本的雕塑形体语言加以凝练以暗喻自我的本初状态。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