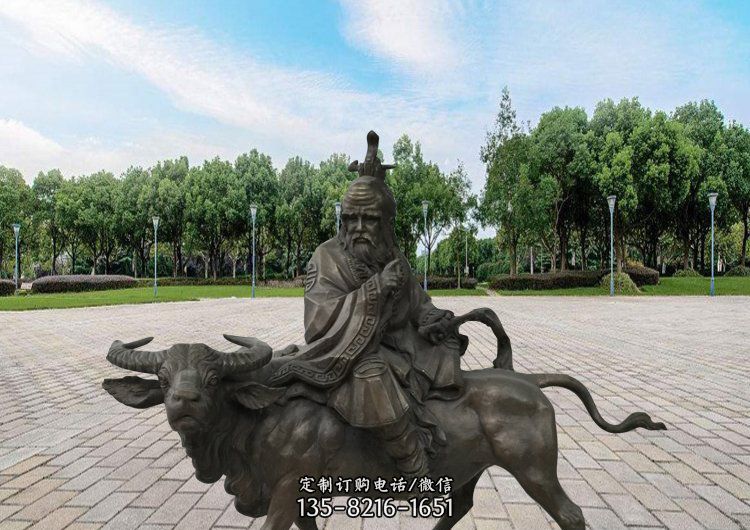
前一天晚上,他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作为全球知名的伦理学家,他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动物的道德处境和人类对待它们的伦理”。这本书在1975年出版,43年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十多个国家掀起了保护动物权益的运动。中国肉食消费量是全球最高,这场运动在这里进展缓慢。可是,一旦更多人认可辛格的动物保护伦理,其蕴藏的变化潜力最大。近年来,中国的素食者增多,尽管部分人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但客观上减少了对动物的损耗。

8月13日辛格到达北京的这一天,《动物解放》的中文修订版刚好新鲜出炉。8月17日早上,辛格在哲学大会发表演讲,下午在清华大学与学生交流。在爱吃肉的国家推动素食,呼吁不杀戮动物,是一件艰难的事情。2012年辛格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6年后,他再次访华,中国仍然没有关于动物的全面保护立法,养殖动物的环境仍然缺乏法定标准。

他在哲学大会的演讲特意从希腊传统讲到中国的佛教,引用中国人熟知的佛教文化,“如诸佛尽寿不杀生,我某甲亦尽寿不杀生”,主张“对动物应抱以同情”。他认为世界上的物种应该是平等的,不杀生是体现平等的最好策略。但同时,出于效用主义,辛格的伦理学还包括主张机构慈善和父母有权剥夺严重残障婴儿的生命。这使得成为在世的最受争议的伦理学家,曾被《纽约客》称为“危险的哲学家”,基督徒和残疾人运动者激烈地批判他,认为他的理论残酷且冷血。

批判者曾经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施加压力,反对其为辛格授予教职;辛格认为,哲学家就应该被质疑和批判,就像科学家需要实验室的反复印证一样。在他的眼里,有些反对者是错误的,有些是误解,有些是有价值的,后者会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伦理主张和表达。半年前去世的哲学家曾经对辛格提出了批判,辛格承认他“很优秀,想得更远,更深刻”,从而修正了曾经旗帜鲜明的主张“任何动物不可杀戮”。他举例说,一个家庭以获取肉食为目的饲养动物,为之提供了人道的环境,如果有人反对杀害,那么会有别的动物被杀害。

对于这种情况,辛格自称抱着更加灵活的态度,不再坚决反对。8月17日下午,他和清华大学学生交流,回答了很多人生困惑,也回应了诸多的伦理质疑。活动完毕,他坐着汽车离开,融入了北京周五的晚高峰。回到酒店,桌子上整整齐齐地堆满了需要他签字的待售新书。我们见面之前,他换上了蓝色的纯棉衬衫,灰白色的休闲西裤,系上灰色的塑料腰带,黑色的仿皮鞋。他认为衣服的功能是遮羞保暖,除此之外的追求都是多余的。

在富力万丽酒店的行政长廊,辛格坐在一个会议室里,接受一个又一个记者的采访,问题类似,答案也是部分重复的。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在楼下餐厅吃面,同行的还有我6岁半的女儿桐桐。前一天晚上,我一边准备采访提纲,一边和女儿讨论辛格的伦理主张。辛格说物种平等,人和动物是一样的,如果人不能吃兔子,那么狐狸也不能吃兔子。另外,辛格说严重残疾的婴儿可以被杀死,如果那个婴儿是他自己的孩子,问问他,是什么感受?

征得辛格同意后,我决定让女儿旁听采访,亲自听听辛格的解释。我爱吃肉,不可一天无肉,对辛格的素食主张本来不感兴趣。8月初的一个晚上,《动物解放》中文修订版的策划编辑景雁先生来到正午酒馆。我和他一起喝了一杯台湾的金门高粱,他对我说了辛格是“当代最受争议的活着的哲学家”。可能因为醉意,也可能因为好奇,我突然想看看一个“冷酷”的哲学家是什么样子的,也想听听他是如何回应世人的质疑。特别是当一个肉食动物坐在他面前,他会如何说服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笑眯眯地坐下来和我女儿打招呼,眼睛弯弯,嘴角上扬。我很想知道他在效用主义的理性之外,在私人生活中曾有的心软时刻。他说起了他患肺癌的姐姐,每月做检查,监测病变,结果出来之前,他总是忍不住地担心。偶尔,孙子去澳大利亚的家里看望他,扑到他怀里,表现出对他的亲密,要他陪伴阅读。他看着一个小人类慢慢地长大,做着一些美好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很温暖。他还记得女儿12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放学,晚了几个小时还没回家。

警察到了家里,在询问各种细节的时候,女儿开门进来,完整无损。我问他,既然人类和动物都是平等的,如果只有100个警察,是应该把他们派去寻找失踪的女儿,还是寻找100只失踪的狗。他说,当我们讨论生命的价值时,很难去比较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众所周知,人类的生命对未来是有抱负,有计划的,动物是没有未来导向的。我们不可能论证,多少个人类的生命价值等于多少只狗。但是,在肉体感受痛苦的知觉方面,人类和动物是容易比较的,两者是同理的。

既然人和人之间存在亲密关系,如何挣脱情感羁绊去决定另一个亲人的死亡。大约20年前,美国的《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关于辛格的文章《危险的哲学家》,写到辛格母亲年迈,患了严重的失智症,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记忆,甚至无法认得出家人。但是,辛格和他的姐姐雇请了一个队伍的居家护理人员来照顾,而不是像他在书中所主张的伦理,当一个人失去大脑思维能力,就让她尽快安乐死。

文章说,辛格认为,这个事情让他看清楚了这类问题实在非常困难,特别是当那个人是他自己的母亲,这会更加的困难。不过,多年后回忆那篇文章,辛格认为有不确切的地方,尽管作者非常优秀。在让人倦怠的长时间访谈中,辛格重新振作精神为自己稍作辩解。不过,这需要他和姐姐共同的决定以及和家里的孩子们商量。在那个年代,他母亲所在的澳大利亚地区还不允许安乐死,医生不能开处方,让病人服药或者注射结束生命。
辛格认为,相比于做决定的理性,感性的过程,是更加艰难的。一个曾经活生生的,充满智慧的母亲,慢慢地在精神上不再是他的母亲了,认不出这个儿子,也认不出家人了。《纽约客》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批判辛格自己并不能遵循自己文章里所提倡的伦理。辛格对我很坦诚地解释,他从来不自我标榜完美地践行了书中的伦理,那是很高的标准,他不会去苛责别人,却允许自己做不到。每当讲述完一个观点,辛格的声音就会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尾音,是十分的理性带来的干脆利落。
他和妻子希望回到澳大利亚度余生,和女儿住得近一点。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失智症或者绝症,他和妻子都已经签署了法律文件,委托别人在他们失去了思考能力的时候,让医生开处方,给予药物或者注射,帮助安乐死。他住在澳大利亚,家所在的地区已经有立法允许在病人的寿命预期在半年之内时,医生可以根据病人事先签署的嘱托,实施安乐死。他的妻子曾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她读不了报纸了,请辛格杀了她。辛格说,他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对于他而言,智识的能力和肉身的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如果不能读报,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勉强维持生命,只是浪费地球的资源。
辛格认为,无论在坚持素食,践行慈善,还是选择安乐死,他和妻子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是好婚姻的秘密。几十年前,他决定开始素食,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适应。日常生活中,俩人尽管兴趣不同,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常常达成共识,就是眼光不仅仅聚集在自己是否幸福,孩子是否幸福,而且要努力地让其他人也幸福,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如果说老人的安乐死已经逐渐被世人接受,那么安娜·麦克唐纳的故事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伦理困境。安娜出生于1961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是一名脑瘫患者,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发出的声音像鸟叫。3岁的时候,被父母放进墨尔本一家专门照料严重残疾儿童的医院。16岁的时候,体重才24斤,不过被一个作家兼残疾人权益保护者发现了她拥有沟通的能力。后来,她在脖子上架着一个字母板,大腿放着一个电子控制器,通过高智能的设备和外界交流。
最终,她向法院申请离开了特殊医院,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根据辛格的伦理,她在出生的时候,就属于应该被“杀死”的婴儿。我问辛格,当他看到安娜的那句话时,对自己主张杀死残障婴儿的伦理是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但是,如果当她还是婴儿时,父母决定剥夺她的生命,是符合公义的。辛格说,安娜在另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在她婴儿期就被终止生命也许是更好的事情,尽管她目前享受生命,但是把她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并不是一个好的生命体验。
可是,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安娜批判辛格说,她和辛格之间最原则性的冲突是,如何决定一个残障人士可能实现的生命。如果你知道,未来的生命是非常荒凉和充满痛苦,那么辛格的伦理是有效的。辛格并不了解个体,在他眼里,残障人只是某一类人群。你可以说,让所有严重残障的生命都生存下去吧,毕竟未来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变好。如果,可能性太小,你也许就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那个生命延续,意味着漫长的痛苦。他自称,已经和很多人残障的人士和家庭交流这个伦理观点,可是遭到很多误解。
你可能错误地杀害了一个婴儿,也可能错误地保存了一个婴儿,让他的一生饱经痛苦。医生也不是,当他走出诊所,走下手术台之后,他对婴儿就不再有照料的义务。这个义务在父母,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的福祉,他们才能对孩子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相比于遗弃,在理性考虑之后,终止残障孩子生命的行为是更加负责任的,因为是父母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对孩子而言,是更好的方案。而遗弃,会把孩子留给了不确定性,不知道是否会有新的负责任的人来照料他。
多年来,辛格的这个伦理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基督徒基于圣经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他声称并不膜拜圣经的权威。但是,他对于残疾人的呼声是理解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修正了相关的伦理表达,让其更加温和和清晰,减少众人的误解。如果国家有保障,社会能提供帮助,父母可以判断孩子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孩子未来的生活处境太艰难,那样的生命可能就不值得延续下去。生存与否,决定权应该在父母的手里,他预设的前提是父母爱孩子,而且相比于医生和其他人,父母是未来长期照料残障孩子的人,他们才是为孩子承受重担,并且需要负责任的角色。
辛格提倡慈善,将收入的30%左右捐给慈善机构,可是经过路边的乞丐,他不为之侧目,也不施舍。但是,交钱给慈善机构,他们可以雇请人员,用数据分析,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让我的金钱最有效。中国的发育得并不成熟,缺乏信用,很多人就懒得去甄别慈善机构了。我问辛格,如何看待他的伦理观点成为很多人拖延或者不做慈善的借口。中国以后也许会有更好的市民社会,更好的慈善机构,人们可以信赖的。
在西方社会,有市民社会,可以让人更多参与慈善事业。他认为,做慈善,是需要理性分析的,并不是仅仅出于内心的怜悯,在瞬间做出反应。孩子是被利用的,是乞讨的广告,这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孩子应该去学校。如果大家伸手行善,就会鼓励更多的父母或者成年人利用孩子来乞讨。每年最后几个月,他会和妻子讨论把钱捐给哪个慈善机构。他们把收入的30%都捐出去,同时,辛格父亲给他留下的信托财产,有一部分也被用于慈善。
有时候,他们会衡量,在改善人类贫困的机构和改善动物处境的机构之间,应该如何决定金钱的比例。无论如何,辛格都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仍然相当舒适,可以继续提高慈善的比例。我很想弄清楚,辛格做慈善是否因为出身优越,衣食无忧,所以有能力慷慨。他并不否认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数量可观的财产,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工资,出版的图书,足可以做慈善。他说,很清楚,很多人没他挣钱多,可是只要买得起瓶装水的人,就不算穷人。可是,中国社会缺乏保障体系,如何能让人放心地把收入捐给别人,而不让自己陷于经济风险?
辛格说,当然应该给自己留一些储蓄和买保险,保障医疗和教育。当人仍然有能力买好的衣服和奢侈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能力做慈善。就算是哲学家,也要遵循俗世的普遍规则,并不能经常用效用主义的思维来计算得失,特别是对家人的情感回应。5点15分,我和另外一个记者一起去他的房间接他,一起坐地铁去吃晚饭,然后参加七点钟在北京芳草地中信书店的新书发布会。当我们敲门的时候,他已经做好准备,随手拿起一件黑色的夹克,就一起出门了。
他很友好地弯下腰,一边走一边笑着用英语说,“人类不吃鸡还可以吃青菜,可是狐狸不吃鸡,就会被饿死,所以,狐狸可以吃鸡,而人类不可以。”我们大概六点到达了吃晚饭的素食餐厅,席上还有国内几位研究动物保护的学者和家属。我点了一份6人套餐,其中一份饺子配了类似老干妈的辣椒酱。餐桌上,有假装松子鱼的糖醋茄子,假装香肠的土豆泥,还有青菜煮蘑菇的汤,没有一个让我有食欲。
可是,辛格每次举筷都没有犹豫,好像食物在他眼里无差别,吃得津津有味。饭桌上没有客套,辛格自己夹菜,放进自己的盘中,一一把食物都吃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饭菜打包,他感慨一声,“幸好有人把食物带走,我害怕浪费了。”稍定情绪后,他和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就分别演讲,主题再次围绕动物保护。听众很踊跃地提问,结束后,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签名售书。夜里十点左右,辛格快速地完成这个环节,着急回去酒店。
他次日要赶8点多的飞机去欧洲,和妻子有几天的假期。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