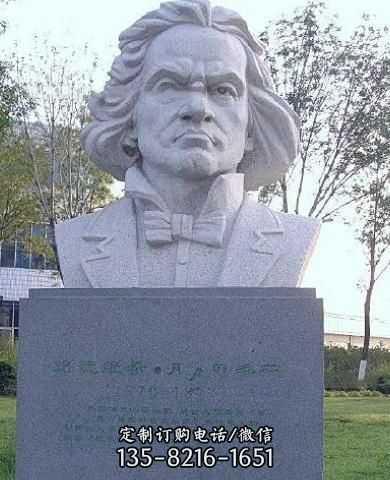
”在奥尔德堡举办音乐会的头一天晚上,这位钢琴家告诉了笔者他为什么总会撩拨和刺激到传统主义者和评论家们。谁能想到,英国喜剧演员诺曼·威斯登会在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遇到最忠实的粉丝群呢?克里斯蒂安·扎哈里亚斯可能名扬欧洲,但他的英国粉丝却不在伦敦:他们在奥尔登堡,更多的是在苏格兰的东纽克,他正要于此地举办年度系列音乐会。

这位德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总是把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演绎得别出心裁,也总是激起声声反对,因而我打算找到他进行采访。其时他正和我近在咫尺,就住在斯皮塔福德艺术家区的一幢排屋里。他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举止随意也很随和,但是他住处的开敞式装修风格,那些精心摆置的绘画与雕塑,都尽显其坚持清爽整洁的审美诉求。得知我的来意是要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后,他很快便跳过老生常谈的开头直入正题。他有天分但并非天才,一直觉得钢琴是难以驾驭的令人生畏的乐器。

“我发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有一位享誉国际的钢琴家,最多也不超过两位。所以从逻辑上讲,成为一国首相的可能性倒比成为该国的顶级钢琴家更大一些。”但是他在比赛中表现出色,所以决定先努力到25岁:但如果到了那会儿我还得坐等举办音乐会的机会,我就放弃弹琴去做别的。”到了25岁那年,最后关头,他在久负盛名的拉威尔钢琴大赛中夺冠。为了增加事业上的胜算,他那些年也一直在进行指挥方面的训练。所以理论上讲他当时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但他严于律己的人生信条使他未能继续。他说,干指挥这一行是需要有权威的,而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四十多岁才可能被接受。

“站在60位顶级职业音乐家面前,告诉他们要怎么去演奏,挑战太巨大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钦佩教师们——我可应付不了16岁的顽劣孩子们。指挥家太年轻的话,是一件反常的事儿,挺奇怪的,可是大家都想找到新的西蒙·拉特。“他们想找到的人需要有多年的经验,出头露面太过是危险的——你得有能力说,不让我安静半年吧。”说来也怪,这正是拉特本人前不久给这位委内瑞拉年轻人的建议。肖邦曾是扎哈里亚斯的曲目大宝库,但他说如果现在他弹肖邦的第一部练习曲的话,那些曲目“可恶的”技术要求会彻底毁了他的双手。不过他对这位深受拥戴的作曲家有别的更为反感的理由。

“只要我弹舒伯特,就不能弹肖邦,他们两人的作品弄不到一起。唱一首肖邦圆舞曲或者夜曲,紧跟着唱一首舒伯特的旋律。你就发现肖邦的曲子听起来土气又做作,但是舒伯特就是从心而发的——他懂得歌唱的意思。“他的赋格曲听了开头就知道后面,让我觉得无聊”,说着他还嘲弄似的地唱了一行巴赫的乐段。”他认为舒伯特的长篇钢琴奏鸣曲和布鲁克纳的巨型交响曲是“每分钟都在起作用的结构,而演奏巴赫的《英国组曲》则会让我开小差。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他曾录制了一张名为《没有赋格的前奏曲》的。可是我觉得,坐下来把所有的调都有条不紊地弹一遍,那才是挑衅——简直疯了,就好像你带着一本字典读给观众听一样。”不过此人并不在在乎乐评家们怎么想,他只在朋友转发给他时才看看那些评论。”我说我觉得他把贝多芬最为精雕细琢的奏鸣曲演绎得就像是现场即兴一样,他听了倒挺高兴。也不是说每次我都要把它弹得不一样——我还是喜欢自己的即兴有组织有条理——但是只要能保持住自由的感觉我就很高兴了。

重要的是不能像某些钢琴家那样最终缩进了越来越完美主义的小格子里…“那样,没过多久你就得开始自己调琴,到了最后你得用七架不同的钢琴来实现不同的效果。那完全是个死胡同嘛,与艺术与生活与别的什么都没啥关系。“艺术必须是完全开放的,而且只要是你做的是人力所为的事,就没有完美可言。”本着这种思路他算是认可了自己的成功,说到这里他疾步踱着小圈儿轻拍双手喃喃自语,好像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得有多好似的。他喜欢在东纽克演奏,原因之一是他能在这儿风格古怪的乡村场馆中营造出一种亲近感。

指挥家们都不肯把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放到一场演出的最后,原因是它的结尾部分声音极弱,他们担心结束后会无人鼓掌。”最后我们随便聊了聊身边摆置的各种艺术品,从艾伦·琼斯的波普艺术到斯皮塔福德的制帽匠的模具,还有一大堆不好归类的民族艺术作品,以一幅硕大神秘的印度野猪画为代表,他解释说那幅画大概有两百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两尊坐佛的轮廓。可能最开始这是一幅宗教画,但是时间一长磨损褪色,所以后人就用这画布画了别的东西。

”所有这些都是这位生活在年轻英国艺术家圈子里的音乐家亲口所言:音乐领域也罢,美术领域也罢,他都是一位极富热情的挑衅者啊。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