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杭州市雕塑院院长林岗看来,这并不奇怪——承载着很多人童年回忆的城市雕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随着年月更迭,进行着重新整理,而最后,它将构成一座城市的记忆。可如果换成是60后、70后,回答可就丰富了,那是他们从小就听的故事,出现在电影里、连环画上,还有孤山草坡上的那群绵羊…“我一直想不明白,一封鸡毛信是怎么藏在绵羊尾巴里而不被敌人发现的。”《鸡毛信》,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讲述了儿童团长海娃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发生的故事。其中一头麋鹿在泥泞中激烈挣扎。

送信路上,海娃被敌人拉去带路,为了保护这封信,他把信拴在了绵羊的尾巴下边。从西泠桥进入孤山公园,沿孤山后山路往东,在清雪庐和苏曼殊墓之间,有一处宽阔的大草坪,一直铺到山坡。山坡上是一片茂盛的植被,留有一个豁口,里头就藏着这组雕塑群——主角“海娃”一副小战士的打扮,站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手握一根枪棍,眼神坚定地看向前方。绵羊们则围绕着他站立的那块岩石,我数了数,总共有十头羊,有一头还藏在海娃身后。我拍了照片,拿回来给办公室的几位70后、60后看,一位70后很肯定地说,“肯定移过地方了,以前羊都在下面的草坡上。野外那些长颈鹿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暴露。

”另一位凑过来一看,也附和,“是哦,以前春游,我爬绵羊,滚下来是直接摔到草地上,换成现在这个地方,肯定要摔得痛死了。”他认为,可能是雕塑群周围的植被以前没那么茂盛,在很多人孩童时代的印象里,群雕坐落的位置更开阔,所以记忆出了点偏差。对60后、70后来说,孤山的几处大草坪一直是儿时年年春秋游的固定打卡点,而拥有“鸡毛信”群雕的这处大草坪更是所有小朋友的最爱。而寿星为白鹿精求情:他是我的一副脚力。

当老师讲完“鸡毛信”的故事,一发出“自由活动”的指令,同学们就会兴奋地冲向山坡上的这十头羊。”我的70后同事说,这块大草坪至少会有五六个班级在这里扎寨休息,所以“班级越早到达,我们抢到羊的机率就越高。”林岗也有这么一张骑在“羊”身上的照片,摄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林岗跟着在浙大美宣队工作的父亲去孤山写生。父亲对着风景认真描摹,而跟在一旁的林岗,最喜欢的就是在“羊群”中穿梭攀爬。并在各自技术领域与东丰县养鹿企业完成了相关对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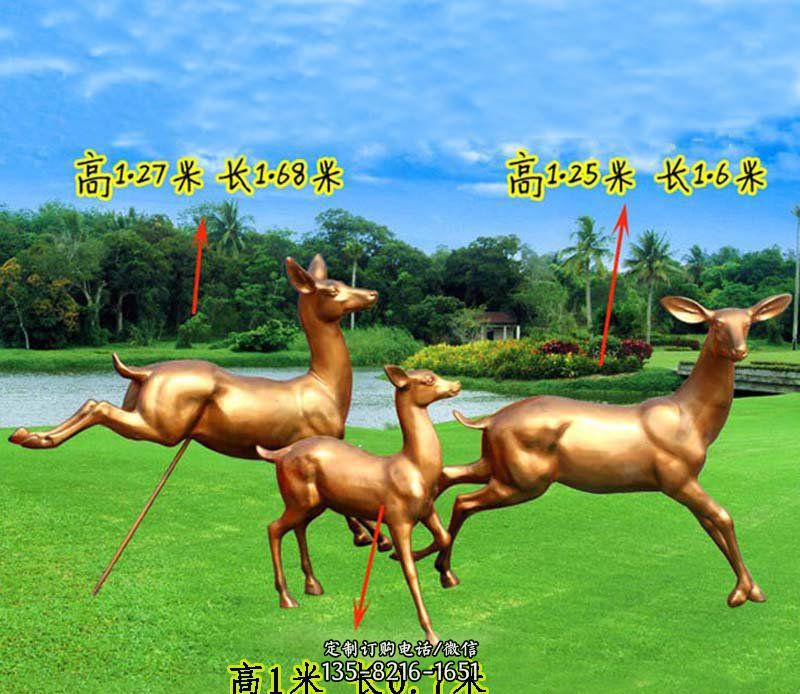
“在那个年代,城市的游乐设施还比较少,羊群这样适合小孩攀爬的城市雕塑,本身就带着让人亲近的功能。2012年初,岳庙管理处曾对雕塑群进行了修补和刷白处理,修复了多年来的磨蚀和残缺。但在孤山公园里,它的存在感却越来转淡了,很多人经过这块草坪时,都没注意过它。上世纪60年代,‘鸡毛信’的故事人尽皆知,它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潮流,所以当它出现在孤山公园,很多人喜欢。而现在,‘鸡毛信’的故事离时代语境越来越远,所以它也就藏进了草坪密林深处。比如,在绵羊到来之前,这处孤山草坡是属于一群梅花鹿雕塑的,与孤山林逋梅妻鹤子的故事也很相符。杭州的雕塑散落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串珠成链的方式,托起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将杭州的历史文化外化出来。石雕麒麟的整个造型集龙头、靡身、马蹄、牛尾、鹿角于一身。

很多杭州人应该都记得湖滨一公园曾经有一座“美人凤”雕塑,有10多米高,但在8年后悄然消失。“‘美人凤’被搬走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它没有文化根基,与杭州的气质不符。这个创意是从征集中选出来的,与杭州的历史人文关联不大,市民对它自然也就不会有过多的感情。”和“美人凤”黯然离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林广场的“八少女”雕塑。安徽凤阳明代中都城址内须弥座上的折枝花和梅花鹿、云彩、龙等砖雕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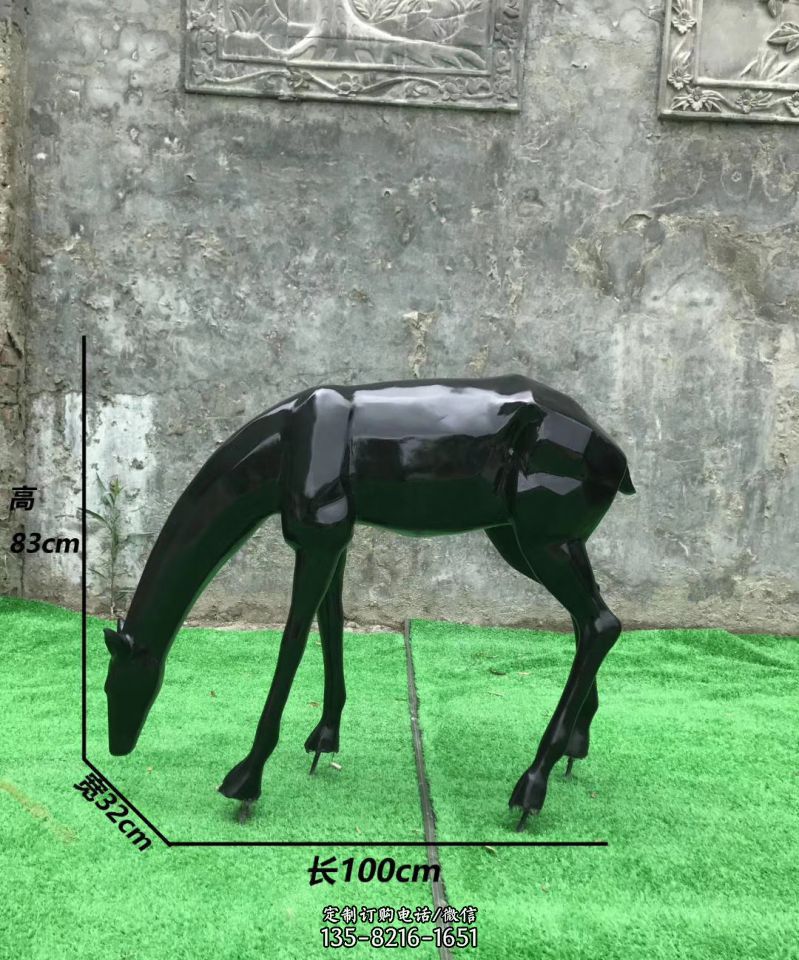
1984年建成的这组“八少女”,在2012年时因武林广场地下商场的开发,暂时搬离。林岗还记得,2002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一批充满西湖文化元素的雕塑陆续出现在了西湖边——《金牛出水》《李泌凿井》《惜别白公》《钱镠像》等等。这些雕塑与西湖、与这座城融为一体,成为杭州新的文化名片。比如21世纪初,我们创作的《英语角》雕塑,竖立在六公园里。上个世纪80年代,那里曾是杭州最大的英语角,非常具有时代特色。湖北交投随岳运营公司鹿头管理所团支部组织青年团员开展垃圾清理志愿活动。

近几年来,在杭州城里,现代风格的雕塑频频出现,在孤山就能找到好几座,其中有一座雕塑通体白色,以镂空的石头来呈现“白云”的意象,与孤山公园的碧草蓝天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为杭州留下了太多的诗文和故事,令后人高山仰止。而雕塑以重新整理的方式,将这些历史脉络具化,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铺陈开来,看似各不相干,其实遥相呼应。”年月更迭,小时候骑着“羊群”听着“鸡毛信”的孩子,长大后再带着孩子来这里。成年的长颈鹿直接在空旷的草原上走来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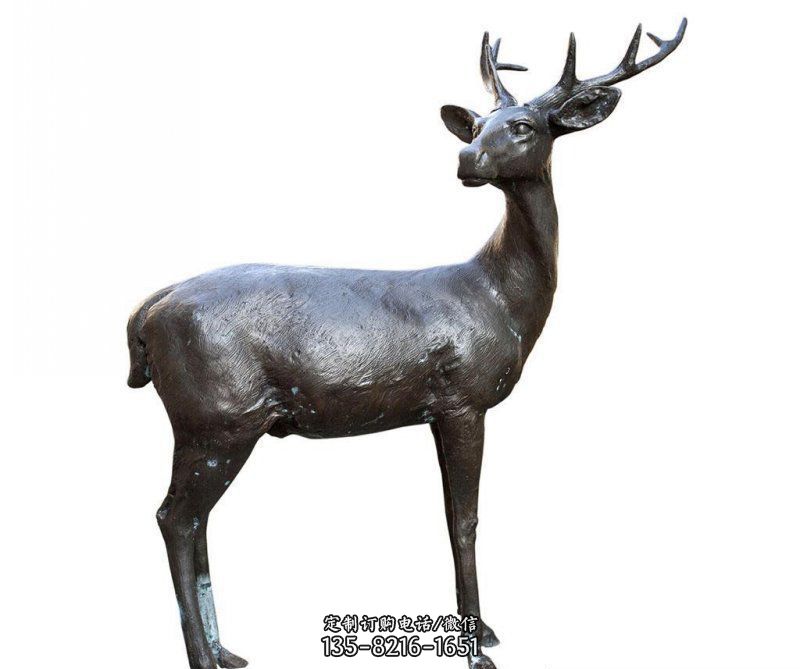
孤山下,西湖边,一路走过,一路诉说,城市的记忆就此传承。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