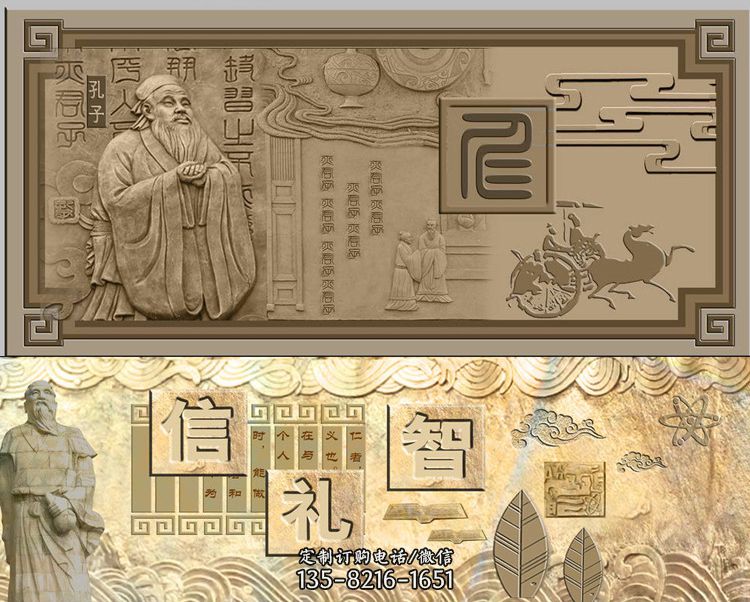
直觉就是当下最灵敏的感受,灵感是外在力量在内心的投射。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与评价,倾向于是一种个人体验,无是非对错可言。在迈耶·夏皮罗教授所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一书中,对绘画作品的风格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严谨和细致程度不亚于微积分理论的求证。他更是在书中,对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写过的艺术评论进行了“纠错”,堪比文艺界的“方舟子”。迈耶教授在有关理论的讨论中,经常提到再现能力的重要性。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孟子胸像铸铜雕塑虽然其近一两年来。

再现能力通俗的讲,就是临摹和写生的能力,将眼睛感知到的事物,通过手和笔,重现于纸或其他介质上。如果我们去临摹一幅书法作品,将临摹的目标定义为肉眼看起来越像越好,还是气质上把握的越精准越好?中国的书法临习者,两者都会侧重,不过更倾向于“意临”,也就是重点取其趣味,其次在外形。如果按迈耶的看法,他会认为将字形临摹的精准,是书写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天赋。追求再现能力,听起来枯燥乏味,是被倡导意境的人所不屑的。而单纯的追求意境,容易陷入浮躁与空虚之中,缺乏同现实相连的力量感。任何有理性的、谨慎的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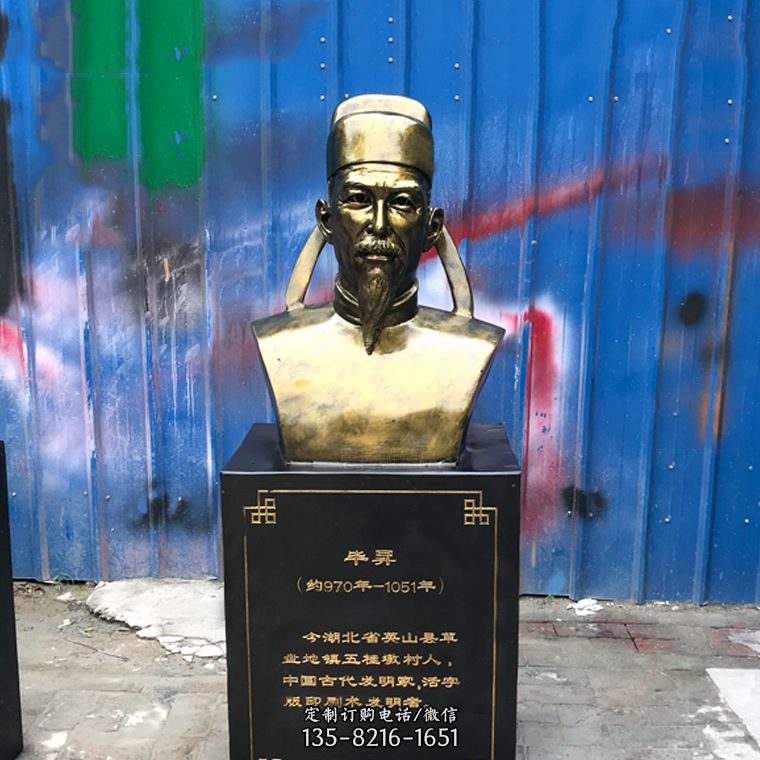
迈耶在书中写道“对自然形式的再现一直是许多文化中的艺术目标”。不过,迈耶认为中国古代雕塑中对人的眼睛和衣纹变化的再现方式,是受到了古希腊范本直接影响的结果。对于这一判断,相信许多民族主义者会站出来进行质疑。关于艺术品的风格,迈耶并没有给出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朱良志所著《南画十六观》中,用十六个关照点,便描述了十六位文人的真性情。是和科学家、哲学家一个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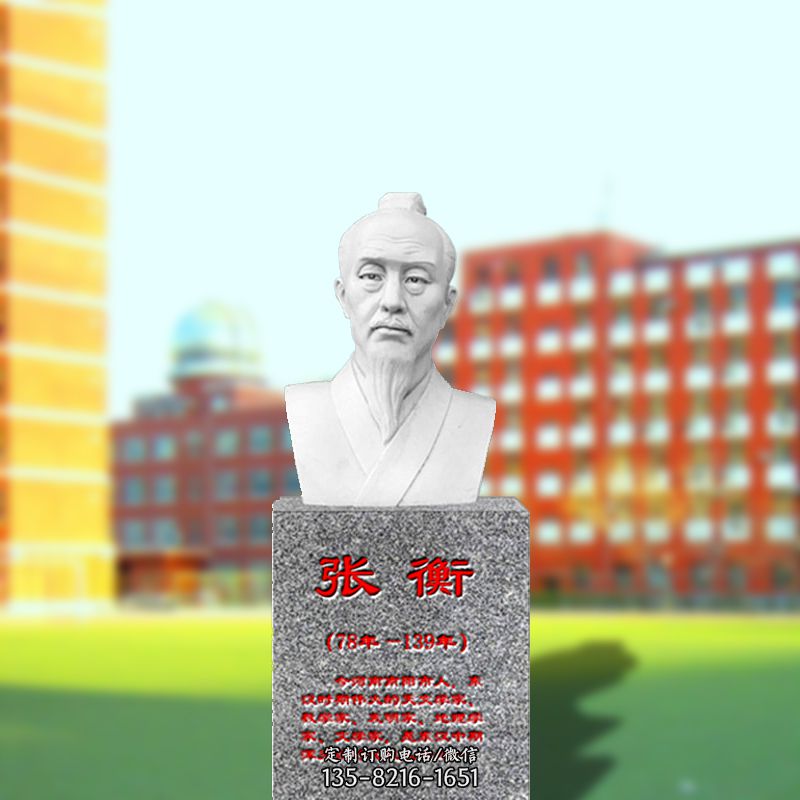
迈耶的科学精神和朱良志的“真性”,从不同的方面帮人们理解艺术。作为画家和作家的合体,欧仁·弗罗芒坦着实被迈耶认真的剖析了一番,看的人直冒冷汗:“他非常清楚的感到,作为一个画家,他的问题深深地根植于他的人格,根本不是来自往昔艺术的灵感可以解决的”“他就写出这本书,比他的那些精致的画作更好的代表了他的天赋”。哲学家海德格尔同样避免不了被迈耶抨击,只因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解读了凡·高所画的一双旧靴子。哲学家可以继续他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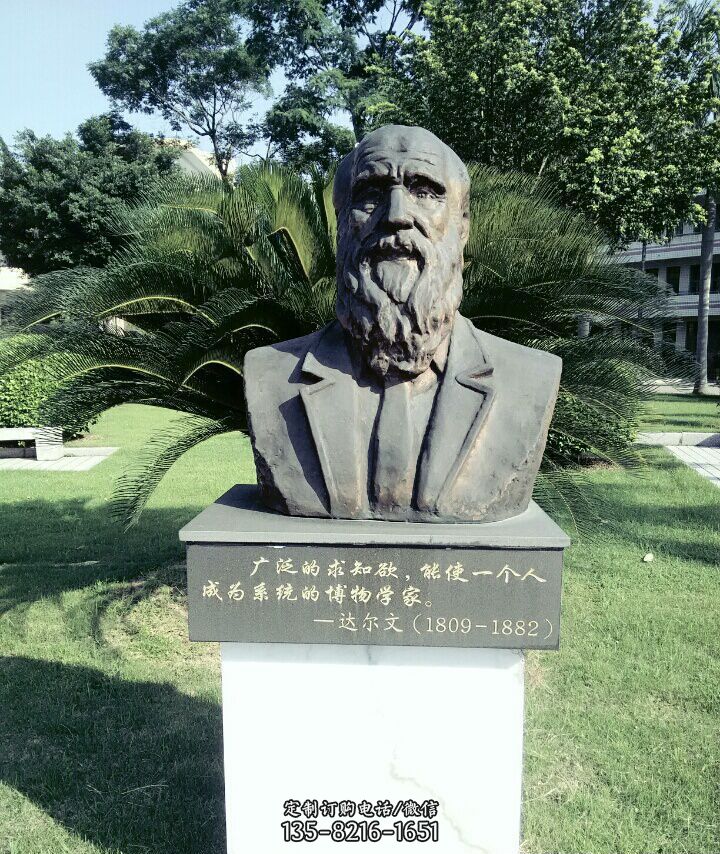
海德格尔认为这双靴子是农妇所有,用充满感染力的语言渲染了农妇的生活状态“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迈耶毫不留情的嘲讽了海德格尔对这幅画形而上学的解释,认为海德格尔在评价画作时,忽略了艺术家本身。据迈耶考证,这双鞋是凡·高自己所有,并且对他有不一般的意义。凡·高的父亲是一名牧师,他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相关的知识,为自己将来从事这一行业做着准备。他曾经瞒着父亲,到工厂里去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做牧师的工作,这双靴子陪着他度过了艰难的长途跋涉,是一个神圣的遗物。那么他可能是一位伟大的地平说哲学家。

迈耶指出,海德格尔“在于作品的接触中,他既体验到了太少,又体验到了太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中,研究了达芬奇有关童年的笔记,并由此推断,达芬奇笔记中的秃鹰是母亲的替代品。迈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达芬奇笔记中的这段文字,并非他自己个性的彰显,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模式。迈耶在《狄德罗关于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贝伦森先生的价值标准》、《论赞助人与艺术家的关系》中,传达出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担忧和情怀:几乎是一班希腊哲学家与艺术家共同的论调。

狄德罗是法国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迈耶评价他“在自由中既看到了其个体的层面,也看到了其社会的层面,而且他还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过,狄德罗没有意识到,规定的任务并不意味着是对自由的侵犯,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由王公贵族向艺术家定制后面世的。不难看出,迈耶并不认同贝伦森那般,“将文化作为商品加以利用”的生存模式。将贝伦森的传记《个人肖像速写》评价为“一次经过巧妙处理的不安告白”,“他和他的良知展开搏斗···正是这种孤单感和挫败感,打破了他自画像中的那份宁静”。黑格尔看到了洛克一类哲学家的真理观的缺点。

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理想模型应当是这样,“赞助人给与艺术家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追寻他的艺术灵感”,但传统的艺术家很少会如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一样,会在没有定制的情况下自发的创作。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