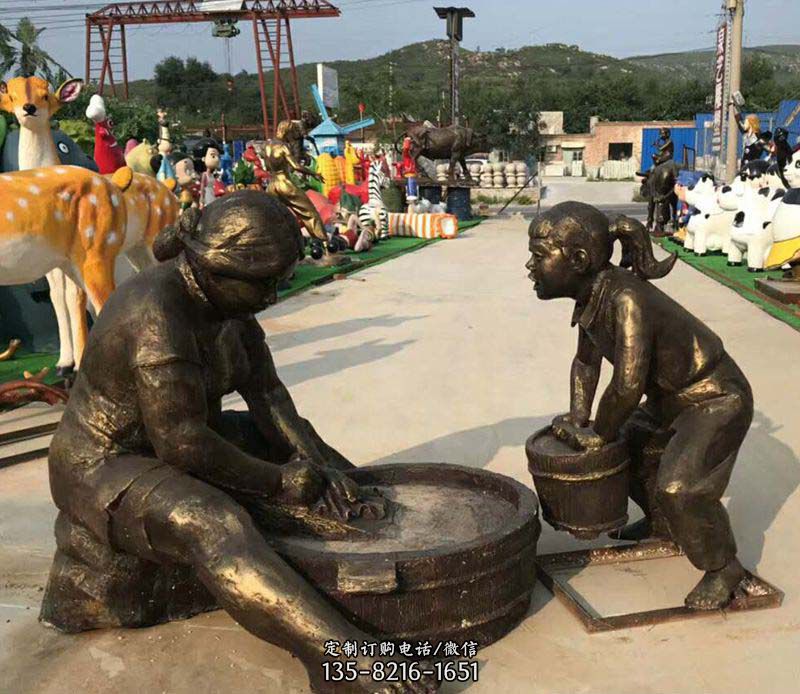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末的巴黎,有人在塞纳河边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个年轻男子推着一辆手推车,将车上装得满满的雕塑品倒进河里,那正是已经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圈成名的瑞士人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他的怪异还不止如此,白天他做了作品,到晚上又毁掉。这种习惯持续了一生,一件作品被他反复修改,不断推翻重来,到最后完成时,往往已历经好几年。创作中的贾科梅蒂总觉挫败,对此他深感困惑——在工作前,他似乎看到一个面貌清楚的男人或女人雕像就在眼前,可一旦开始动手,却感觉迷失了。

所以始终不满意的他只能坚持工作,夜以继日,只为追求他眼中事物那“正确的”尺寸和比例。位于路易威登北京文化艺术空间的一个玻璃展柜里,三个行走的男人相聚,比旁边一个横在杆子上的头像大不了多少;另一个玻璃展柜里是同一个男人的一个头像、两个坐像。人体雕塑的脸部趋于模糊,身体被抽去了脂肪和皮肉,全都异常的细瘦;纤细的人像脚下都有着宽大稳固的底座,从脸部到身体遍布着雕塑家的手不断摩挲的印痕。

偌大的展厅,幽暗的灯光,允许你从容游走在这几位“男人”“女人”之间,心便迅速静下来,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呼吸。这些雕塑的神奇之处是,你离它远时,感到被强烈地吸引,等你走近时,它又在拒绝你,于是你就在这进退失据中不断地徘徊。最先吸引你的是《高挑的女人Ⅱ》,她那么高,你便想回过头去看另一位矮些的《威尼斯女子Ⅲ》。这些作品均为贾氏晚期的成熟之作,是他在“二战”后更加离群索居、蜷缩在工作室里的呕心成果。须知贾科梅蒂不是凭空塑造或绘画,而是面对真人来创作,给他做模特实为苦差事。他的工作室只有20多平方米,堆满作品和绘材,模特只能坐得离他很近,经受他长久的凝视。

久经考验的是他的弟弟和妻子,后来还有法国作家让·热内和日本哲学家矢内原伊甘愿受此“折磨”,甚至萨特也加入了。在伟大的艺术家面前,模特们不仅化身为不朽的艺术品,热内和萨特还成为贾氏最有力的艺术阐释者。贾科梅蒂痴迷于观看,儿时喜欢待在家乡的山洞里对着岩石发呆,22岁到巴黎后眼睛似饕餮,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如初见一般新鲜。他是当年巴黎艺术家泡咖啡馆族的一员,总能发现一些有趣的行人“像岩石一样坚固,又比精灵更自由”,他看得入迷画下速写。

夜里他时常在巴黎街头漫游,只想画出在街头看到的各种事物,作家贝克特是他夜游的好伙伴。他的观察方法很早就不一般,比如17岁时他的静物画把梨画得越来越小,父亲将其改大后,他又再次缩小,惹得父亲生气。近40岁时,他看着一个在街对面行走的女人越变越小,导致他最小的雕塑可以装进火柴盒。对贾科梅蒂而言,面对一个模特没有希望地尽力描绘是一回事,在另外的场合注视眼前的一切是另一回事,这种长年不懈地观察终于催生出他极其强烈又独特的视觉新经验。

1946年,他告诉热内,有一天他看到一条挂在椅背上的毛巾“很孤单,简直可以抽掉椅子停留在原位。从那一刻起我感到有必要通过我的雕塑和绘画,来讲述我所看到的东西”。这种体验似乎带有超现实主义的惊悚,但更像是此前萨特小说《恶心》中的洛根丁的经验:它蕴藏着贾科梅蒂意识的新觉醒,艺术家由此逼迫自己否定既成的雕塑和绘画语言,“削去空间的脂肪”,向存在的虚无迈进,萨特自然成了他的知音,称之为“追求绝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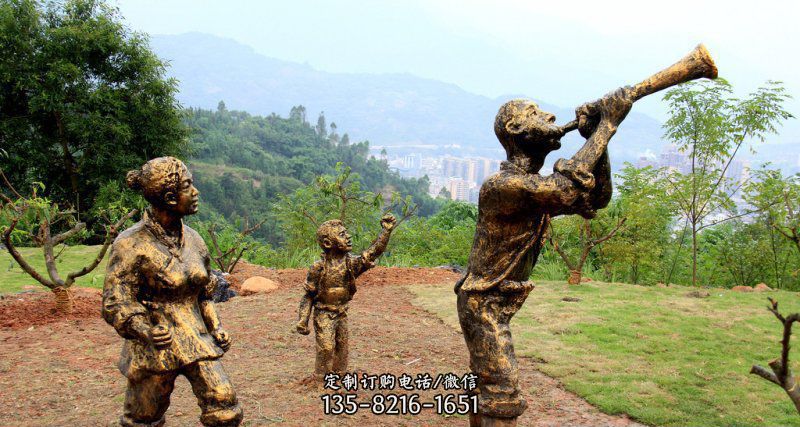
也因为萨特,贾科梅蒂的声名在上世纪80年代随存在主义思潮进入中国。随着他成为全球雕塑拍卖价最高纪录保持者,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在2016年举办了贾科梅蒂在中国的首次大展,多达250件作品到场。诚如诗人里尔克所说,“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但贾氏的孤独并非是那么悲惨的情境,他的“通用人像”提醒人们:人类的“共有灵魂”在远古与未来之间永不停息地往返。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