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当代艺术研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研究对象,廓清这一问题是建立认识论体系的先决条件。前者是有关当代艺术的界定问题,后者是有关当代艺术研究的视角问题,由于互动,两者紧密相关。关于被研究者,当代艺术的界定是个老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迄无定论,因为“当代”一词具有流动性。若从21世纪初的今日时间点来回顾上世纪西方艺术的发展,那么“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二词已然确定了具体所指,即七十年代以前的前卫艺术和七十年代以后的观念艺术。相较而言,任何时代或时期的研究者,都有自己那个时间点的“当代”,随着时间点向未来移动,“当代”一词的所指也会向后延伸,于是永远都有当代,结果“当代”的确切所指被解构。西方学者大多承认并利用“当代”概念的流动性所造成的模糊性,以便给自己的研究对象求取一个可伸缩的时间范围。目前当代艺术圈涌现的新人都或多或少有一定潜质。

《理解当代艺术》的两位作者在该书第一章《导论》中,将“当代艺术”的时限大致确定为1980年以来,但在实际论述中却经常涉及远在五六十年代的波普艺术,甚至涉及二战以前的达达主义。不过,对另一些学者而言,这些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前提,只有八五新潮之后的艺术发展,才是当代艺术的研究对象,例如刘淳主编系列丛书《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便在选文时秉持这一观点。当代艺术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受制于文化思潮和社会变迁,其时限与当代重大社会事件相关,而不能单纯以最近20年或30年来划分。这一因入围作品另类和反传统而备受争议的世界顶尖当代艺术大奖今年却出人意料。

我之所以将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限前沿设定在1979,是因为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是西方文化影响的开始。具体说来,“星星”画展标志了艺术倾向的分水岭,启迪了随后的八五新潮,而与“星星”同时期的伤痕艺术和形式主义,则是中国当代艺术起源的横向语境。这样说来,当代艺术便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思想概念。《理解当代艺术》的作者认为,当代艺术在外观、生产、观念三方面都是非常规的。就我看来,在西方艺术史上,二十世纪之前的艺术大致可以用“模仿论”来解说,模仿便是传统艺术的常规。在代中国当代艺术兴起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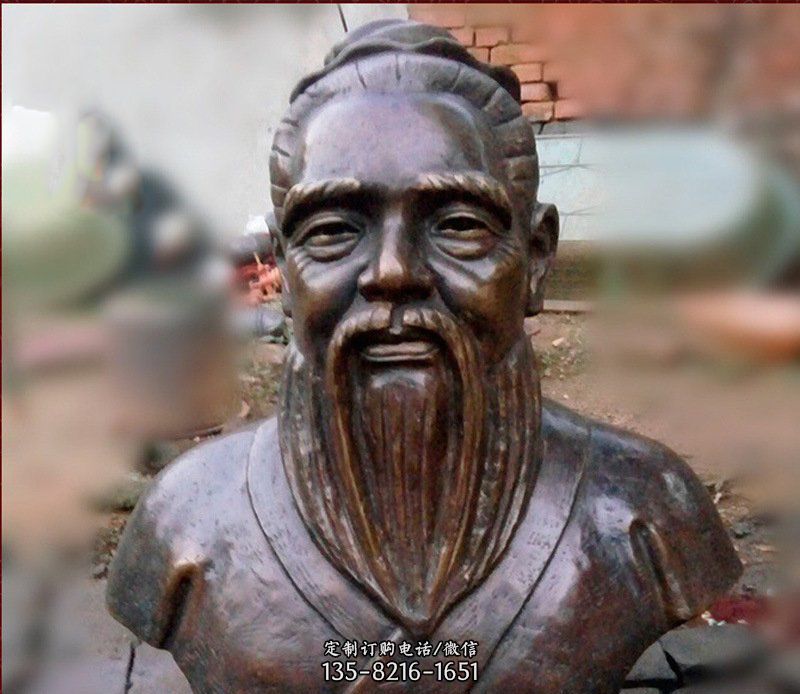
与此不同,二十世纪西方艺术的主流是现代主义,可用“形式论”来解说,形式主义便是现代艺术的常规。当代艺术的“非常规”或“反常规”基本上是针对传统和现代,而对后现代却有所承续,尤其是后现代的观念性。但是,当代艺术并不局限于后现代,尤其是后现代的艺术式样,例如摄影、装置、行为之类,也不局限于后现代的观念议题,例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和环境意识之类。于是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形态被迅速传授和效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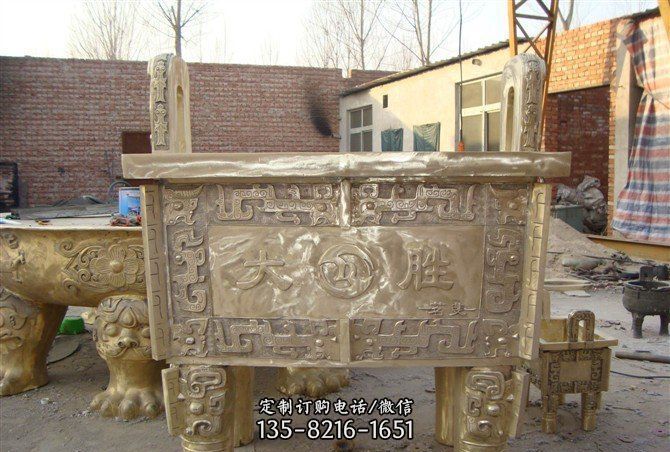
在此,所谓不受局限,是说西方当代艺术虽然承续了后现代的一些外观和议题,但超越了后现代的常规。尽管太阳光下没有新东西,但当代艺术以悖论的方式而拾回了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的模仿论与形式论,并将其转化发展为今日议题,例如“再现论”和“符号论”,这透露了一种开放的观念性。再现论和符号论涉及研究者观照当代艺术的视角和立场,涉及研究者的自身定位及身份问题,其实质是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的区别与关系,换言之,这涉及研究者究竟是艺术史学家还是批评家的问题。不断提炼中国当代艺术的精华。

在时间维度上说,艺术史学家关注过去发生的艺术现象,而批评家则关注刚刚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前者主要进行研究性的学术探讨,不太看重价值判断,因为时间的筛选已经确定了关注对象的价值,除非是想颠覆这一价值以求重新评价。后者同样从事研究性的学术探讨,但主要是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此前尚无判断或判断未获公认。这不仅是判断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是判断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并由此而企及市场价值。这两年舒勇弄的几件东西应该说是引起了人们对当代艺术有了或大或小的关注。

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学者们曾经争论过当代艺术入不入艺术史的问题,在理论上虽未争出结果,但在实践中学者们几乎都将当代艺术置入了艺术史的框架。批评家们一方面要从艺术史学家那里夺取由时间确立的关于艺术价值的话语权,更要将这一价值转化为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一旦进入历史定位的话语系统,批评家的判断就可以决定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市场价值。也正因此,当代艺术批评才对艺术史学家具有无比的魅惑力,毕竟,定价权既关涉艺术家的经济利益,也关涉学者的功名利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才成为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连接点。而他的这种选择正是当代艺术所主张的一种审美判断力。

无论是作为艺术史学家还是批评家,研究者对当代艺术的认识,都受制于视角,即从何种位置和立场出发去观照当代艺术。超越字面而言,视角决定观点,而视角的选择既是观点问题也是方法问题。《理解当代艺术》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两个观点。狭义的历史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目的论,认为历史上的个人对历史发展和历史现象具有重要作用。更好地呼应出当代艺术的美好愿景。

广义的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上下文,主张在历史的定位中确立文化和艺术现象的价值。历史主义者持线性的历史观,从逻辑上说,纵向的线性发展的轨迹可以预测未来,但是当代艺术研究是人文科学研究,不必有数学模式,也不必有弹道计算。这样,当代艺术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便主要是将过往的历史作为当下现实的前提,而不是预言未来。《理解当代艺术》的第二章《当代艺术的史前史》讨论当代艺术的历史前提,其“史前史”一语传递了两重信息:据悉这是展览方为了体现当代艺术就像萝卜白菜一样。

第一,当代艺术可以进入艺术史,其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一部分;第二,当下处于进行时态的当代艺术现象,受制于先前的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历史前提,现代艺术及其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二战前欧洲的早期现代主义和二战后美国的后期现代主义,而作为美国新前卫的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则直接关涉了当代艺术的产生。在此,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理论也是当代艺术的理论前提,因为观念主义者要重拾被形式主义所抛弃的社会决定论和政治主导论。这种非主流的青年亚文化群价值观的变化必然会在当代艺术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如果将西方的后现代艺术视作早期当代艺术,那么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挪用、戏仿和反讽,正好说明了历史前提的制约作用。如果将后现代与当代艺术分割开来,那么前者的观念性对后者的巨大影响,也同样说明了历史前提的制约作用。如前所言,我将“星星”画派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源头,不过我们应当清楚,源头与语境是一体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星星画派所代表的的地下前卫、四川美院的学生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绘画倾向、吴冠中和首都机场壁画所代表的的形式主义,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横向语境,也是历史前提。中国收藏家协会当代艺术委员会艺术顾问。
尽管三者的艺术观几无相同之处,但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稍微扩展一下历史前提的概念,这便是一种文化史或知识史,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和行动史。这一横向的扩展,强调社会文化功能,从这一视角看,制约当代艺术的是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这一视角不同于历史主义,故称新历史主义,此方法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看重社会和文化语境作为横截面而对当代艺术生态所起的语境作用。对经济活动和历史给出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观和人学的理解与阐释。
虽然《理解当代艺术》一书既未使用历史主义也未使用新历史主义的术语,但其观点和方法却无疑具有二者的特征。在第三章《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作者论述当代艺术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语境,首先指出了历史前提的横截面问题,例如,欧洲早期现代主义的野兽派是在二十世纪初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语境中,对作为主导思想的物质主义的回应和反动。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在当代艺术的社会文化肌体的横截面中,占主导的是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这不仅制约了当代艺术的议题,也决定了当代艺术的式样,例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视像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的出现。而且对当代艺术的多元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反观中国,八五新潮艺术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目的,就是要追赶西方艺术的发展。八五之前的中国艺术因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而比西方艺术的发展落后了整整一百年,新潮艺术家们的责任便是追赶西方,于是在1979-1989的十年时间里,中国艺术家们拼命模仿或借鉴西方艺术。这种共识和追赶,由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决定,是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大势所趋,呼应了当时工商经济和科学技术对西方的追赶。自九十年代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现在已跃居世界前列。而不是思想内涵上的当代艺术。
于是,赶上了之后的目的,就是要进入领先行列,故有“与国际接轨”之说,全球化和本土化成为主导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成为艺术家们的集体焦虑。为了加入国际当代艺术,中国艺术家们拼命“走出去”,大规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甚至不惜花大价钱参加威尼斯外围展。可以这样说,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焦虑,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横向语境。仍然习惯于用现代主义的观念指导当代艺术创作。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传统艺术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要式样,早期现代艺术针对这二者进行变革,给写实绘画和具象雕塑增添了抽象的形式。后期现代主义另辟蹊径,打破绘画和雕塑的界线,推进了装置、行为、概念等新的式样发展。后现代思潮进一步拓宽了跨界之路,延伸了后期现代的地景和行为等形式,衍生出综合式样,并接受了摄影、视像、数字艺术等式样。在此前提下我们不难看出,当代艺术并无新的形式和式样,而是在观念上下功夫。你自己对孙子兵法所理解的认识论。
《理解当代艺术》的第四章《当代艺术的形式》列出了诸种当代式样,也无非是旧瓶装新酒:顾丞峰在日常行为、艺术行为和行为艺术三者的关系中探讨行为艺术,将日常行为界定为个人和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艺术行为”,而艺术行为则是“艺术家所从事的与艺术创作相关的行动”。这两者并不是艺术的本体,而是通向艺术本体的过程和手段。“艺术家以人体为主要媒介,以一定时间长度为单位的演示过程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有预期目的、有观念诉求的艺术作品的创作形式”。探索和扶植当代艺术的年轻力量。
“日常行为与艺术行为容易区别,因为发出行为的主体身份不同,艺术家与普通人容易区别;艺术行为与行为艺术有时会被混淆,因为主体身份相同,但操持的媒介不同,是否通过媒介体现观念,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仅仅有‘艺术意图’尚不足以构成行为艺术的原因,因为即使实施者本人有明显的意图,但充其量也只是构成了‘艺术行为’而并未完全构成‘行为艺术’。”既然当代艺术以观念为主导,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那么我且用21世纪的第一件国际性重大政治事件来讨论行为艺术:提供了研究当代艺术的艺术参考。
那一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其时,有国内来的住校艺术家在一个艺术讨论会上说:本来,美国知识分子以民主开放和言论自由为标榜,给各种声音以机会,但听见中国艺术家的这一说法,主持讨论的美国教授却沉吟了片刻,然后撂下一句话:这位美国学者当时并未解释为什么,可能他还没有从恐怖袭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我也不认同这位中国艺术家的观点,但一时也同样未能理出头绪。十多年后的今天,若用顾丞峰的界定看,首先,恐怖袭击的制造者不具备艺术家身份,其次,恐怖分子操持的媒介与人体行为无关,因此,恐怖袭击不是艺术。笔者并不认为抽象艺术有了一定的市场前景就表明它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虽然我也认为恐怖袭击不是行为艺术,但我可以假设上述中国艺术家对顾丞峰界定的回应,以便进一步讨论行为艺术。其一,恐怖分子不具备艺术家的身份,那么,究竟是某人做出了公认的艺术作品后才被承认为艺术家,还是某人先当上了艺术家,然后才做出作品。这不是一个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恰恰是一个怎样确认艺术身份的问题。其二,恐怖分子的媒介是飞机,这与杜尚的现成品没有区别,而所谓综合材料,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拍品的面更涉及到从欧洲印象派到美国当代艺术等诸多领域。
再者,恐怖分子驾机撞楼的材料恰好包括了自己的身体,而劫持飞机和亲自驾机,则是具体的身体行为。第三,顾丞峰给行为艺术的阐释是“通过媒介体现观念”,恐怖分子正好就是通过以身相撞而表达了对抗文明世界的观念,具有强烈而直接的政治和宗教诉求。1、这并不是一个鸡和蛋先后的问题,艺术家的身份在前,作品在后,比如杜尚的小便器;由于杜尚的艺术家身份,由于特定的艺术界氛围,小便器被视为艺术品,而其他诸多日用小便器只能是便器。
2、恐怖分子使用了自己的身体毁灭了别人的身体,但这不可能是艺术——因为艺术目的不是毁灭自己身体,更不是毁灭别人,艺术是向善向真的游戏,是对精神的超越。但其想法和当代艺术的观念根本不能同一个层面共谈,因为艺术的本质是非实用和非使用的,艺术不能用来作为武器。艺术的观念仅仅是在艺术领域中被描述的,“泛观念”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艺术的观念是一种狭义的观念而不是广义的。
如前所述,顾丞峰关注的是分辨日常行为、艺术行为和行为艺术,他从六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行为艺术:行为艺术是由艺术家主体有计划地做出的,行为艺术是呈现给“艺术界公众”或曰“艺术界氛围”的,行为艺术的出发点应该是无功利、无实用价值的,行为艺术应该是观念表达的载体,行为艺术是有历史时限的,行为艺术的实施应与艺术家本人身体有关。顾丞峰认为,只有符合全部六条,才称得上行为艺术,否则只是艺术行为,甚至是日常行为。恐怖袭击虽符合上述六条中的第一、四、五、六条,但不符合二、三条,因而不是行为艺术。艺术的认识并不是仅仅用条条框框去否定或肯定,顾丞峰的第二条让人存疑,因为艺术的展示对象是所有人,除非行为艺术不是艺术;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助于探索当代艺术的本体和式样,姑且留待有兴趣的学者讨论。
如前所言,当代艺术以观念为主导,但观念本身是个抽象术语,而作品所表述的具体议题才是观念的要义。《理解当代艺术》的第五章《当代艺术的主题与议题》讨论的话题包括:这些话题原本是后现代时期的话题,但到了当代艺术时期已大为推进,例如“秽弃物”便来自后现代以边缘挑战中心的思想。这个术语由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克丽丝蒂娃提出,原本指人的肢体,尤其是不洁和猥亵的部分,不能登上正统艺术的大雅之堂。
由于后现代倡导边缘艺术,过去的秽弃题材获得了当代艺术的青睐,例如今日中国艺术界时髦的变态行为,包括食粪表演。随着后现代“边缘”的扩张,精英主义退化,流行文化得势。在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和文学评论转向时髦一时的通俗文学,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与此相呼应,在艺术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视觉文化研究,标志了艺术史的转向。文化研究是后现代向当代推进的一个连接点,视觉文化研究则是当代艺术研究的通俗化。
这是当代艺术的观念性转向,表现在议题上,便是理论的“推进”,例如在全球化和本土化视野中看待中国艺术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尤其是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转型,一方面受西方现当代艺术和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中国艺术界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其实,我的这一看法也受西方影响,其“影响”观,得益于西方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的焦虑”之说,其“回应”观,得益于西方史学界早前的“挑战与应战”之说。
但是,我没有停留于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理论,而是有所推进。如前已言,我将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阐释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焦虑”和“有意误读”的结果。“误读”是一种选择性阅读,只读自己需要的东西,并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和接受。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切“需要”,一是借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化之机,来为自己的发展提供后勤补给,二是乘机转过身来,利用补给的力量将自己推向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误读使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有可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艺术中探索自己的身份,甚至借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形式而重建自己的身份。
在上个世纪后期,中国政府并不提倡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的前卫倾向具有颠覆性。但是到了21世纪初,中国政府摇身一变,招安当代艺术,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之。招安的策略使当代前卫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对西方的文化主导具有威胁性甚至颠覆性。换言之,当代艺术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有助于中国向外投射自己的文化软力量,有助于配合向外投射经济力量。早在上世纪后半的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曾大力推崇前苏联的地下艺术,以此作为冷战的一种有效武器。
但是苏联崩溃,冷战结束,飞鸟尽良弓藏,苏联的当代艺术在西方一落千丈。不料,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休克和艺术阵痛,普金时期的俄国以能源产业而再次崛起,成为金砖国家之一,艺术市场又获生机。这时候,俄国的当代艺术已不再是西方的冷战武器,而成为俄国新贵的身份和品味象征,无论是当年的地下艺术还是官方的红色艺术,都借市场而满足了今日俄国人的需要,包括怀旧情绪。
中国当代艺术也有类似情况,但中国经济比俄国强大,西方艺术市场也更看好中国当代艺术。在新世纪之前,中国前卫也曾被西方阵营当做冷战武器,例如《纽约时报》曾在1993年发表长文,以栗宪庭和方力均的光头形象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说泼皮的呵欠具有政治颠覆的力量。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政府的招安政策,这股颠覆力量被化解,当年的前卫艺术在消费了自己的颠覆性观念后,利用西方的认可而华丽转身,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又开始消费爱国主义观念,在艺术市场上黑白通吃,风光无限。
《理解当代艺术》的作者说,当代艺术与性产业和军火生意一样,是世界性的缺乏规范的大产业,相当程度上靠人为的黑箱操作,例如艺术拍卖和作伪。作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议题,我的上述黑白通吃的观点可以推进到“文化消费”说。这个观点来自经济和商业界的消费主义,是艺术通俗化的体现。《理解当代艺术》将这个话题同今日大众传媒对文化潮流的主导作用联系起来,并指出了艺术对消费传播的双重态度:早在美国的波普艺术时期,安迪·沃霍就充分利用了消费传播的能量,这之后,杰夫·昆斯将之发扬光大,但又狡猾地流露了一点嘲讽和批判的意图,以免被斥为浅薄。
在中国的后现代时期,王广义利用文革图像所制作的大批判系列,也有类似特征,但他的利用和批判,更增加了一层跨文化的意图。毋庸置疑,王广义、岳敏君之类的后现代手法,例如挪用和戏仿,早泄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影响与应战”的语境中所暗含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焦虑”。到如今,中国的当代艺术已经完全受市场经济支配,由于缺乏自身规范,便只能按照市场原则和方式来运作。今天,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威胁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新的冷战已经悄然打响,当代艺术再次成为冷战的武器,而战场则扩展到了互联网和即时通讯的媒体上。《理解当代艺术》是一部多方面讨论当代艺术的理论专著,但这部书没有讨论当代艺术批评,却是一大欠缺。
不过,此书最后一章从策展营销和购买作品两个相对的角度来讨论当代艺术的市场化问题,提示了艺术批评在两者间所处的中介位置,触及了批评的要义。公元前305年,一个叫菲力塔斯的人到达埃及港城亚历山大,成为国王托勒密二世的私人教师。菲力塔斯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有文献记载的批评家,专长文学批评。究竟菲力塔斯是确有其人,还是像荷马那样是游吟诗人的集体代称,我们不得而知,仅知道批评家可以教育国王。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这位批评家的名字都让我联想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阳具中心主义,这不仅迎合了古代帝王的思想,而且也正好是后现代时期女性主义批评的卖点。
批评可以美其名曰教育,但对当代艺术来说,其实是叫卖,批评家既是卖方经纪人,也是买方代理人。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批评的角色是多维的,可以是喉舌,可以是打手,也可以是掮客,而批评家的身份也可以兼职转换:或戴着大学教授的头衔,或挂着政府部门的官职,或是某基金会的委员或顾问,甚至是某公司的董事或法人。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奇观,是市场经济与政治主导相混合的奇观。当代艺术批评是对当代艺术的有效认识,而从批评的角度去探讨当代艺术,则有益于健全当代艺术的认识论。
西方学术界将艺术批评分为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两大类,前者偏向史论研究,后者偏向时事述评,二者都以认识论为先决条件,并为艺术认识论提供给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因市场和政治原因往往是合而不分,这是当代艺术批评的真相,也是当代艺术的现状,是为认识论。80年代后期任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90年代留学加拿大,后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等校,现任教于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负责中文项目,主讲中国文学与视觉文化,从事艺术史论和比较文学研究,在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诸多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文集、译著17部。
目前写作英文版艺术史三部曲,其中第一部《符号学艺术史:重新阐释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于2019年在英国出版。近年出版的主要中文著述有《读画之道》、《视觉文化:艺术史与当代艺术的符号学研究》、《绘画中的符号叙述》、《视觉的暧昧》、《视觉艺术与视觉文化符号学》等。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