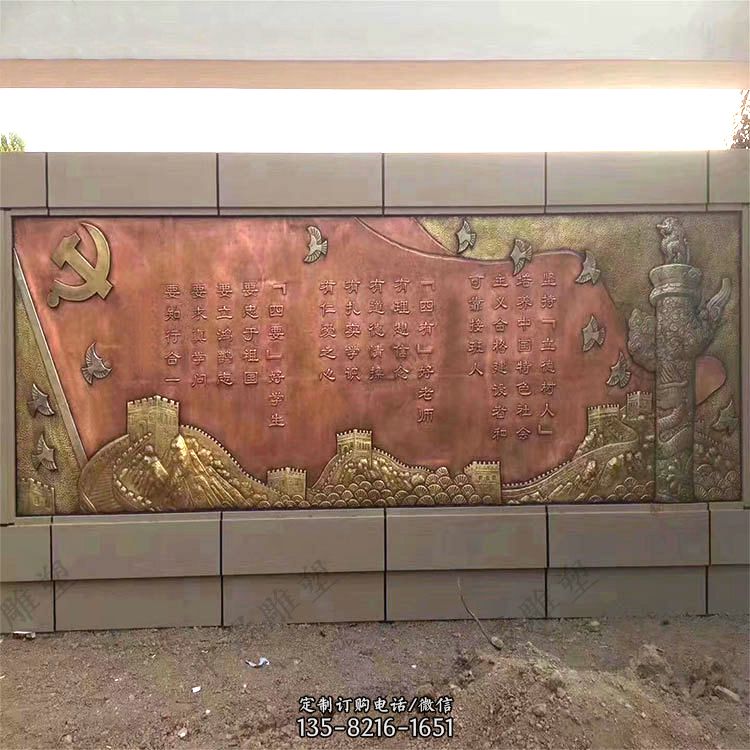
当代国内艺术、设计、色彩等领域深受强调色彩科学认知的西方色彩学说、方法等的影响,而对于注重于色彩精神作用的中华色彩文化的观念、成果等知之甚少,相关研究,尤其有影响的成果鲜见。中国色彩事业若想在世界色彩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地研究、推介、传承和运用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色彩文化,就成为中国色彩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敦煌壁画是敦煌莫高窟艺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过统计的492个洞窟内,共有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作品,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而这些壁画作品的数量之丰富、艺术水平之高则更加为世人所称道!自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发现以来,关于其雕塑、壁画、建筑等各方面的研究一直不断。但在关于壁画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似乎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于画面本身的考证上,却忽视了其基本的色彩表现,讨论敦煌壁画色彩结构及其艺术成就的文章也显得乏善可陈。这或许同传统中国画重“笔墨”、“神韵”有关系,但“笔墨”、“神韵”所创造和表现的都为具体的“形”。”形”唯有和“色”共同合作,方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体,也才能更精确的表现出各种物体所独有的特点。事实上,即使是传统中国画所一直强调的“墨”也有“五色”之分,所谓“墨即是色,色即是墨;

而对“墨”的强调也是随着宋以来文人画的兴起才真正开始的。因此,所谓传统中国画重“笔墨”不重“色彩”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其实每个洞窟的壁画,其绚丽色彩的背后都有主色调统一着画面,充分发挥补色对比的魅力,使壁画色彩之间的充满律动美感。通过对壁画大量的色彩调查,很多学者、专家发现黑、白、灰在壁画色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作为画中不可缺少的中性调和色,它也是使壁画保持色彩鲜明而又和谐的关键。以隋420窟西壁‘维摩诘经变”为范例,壁画以不同层次的粉绿、灰绿与里绿与土红形成对比,此外又以淡紫色与土红色形成冷暖对比。

表现人物时,在黑白的强烈对比下,“文殊菩萨”的一组与‘维摩诘”的基本对称,作为辩论的双方,在用色上有所区别。文殊弟子服装多用土红色与青莲,维摩请弟子服装多用灰绿色。从色彩效果看,“维摩诘经变”色彩结构和色彩纯度、明度的掌握是极有分寸的,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地,使壁画色彩整体的变化、和谐与平衡,显示出画师极高的美学素养。又如北魏第254窟,成功的运用“调和色”,又在适当程度上降低了“鲜明色”的不和谐因素,使画面色彩效果最终达到和谐。

敦煌壁画色彩结构具有装饰性,强烈的装饰感反映出一种热烈而淳厚的民族特性。壁画的色彩结构是按照装饰色彩的秩序来组合色调,讲究色彩均衡、韵律、疏密、节奏关系,把多变的物象概括为平面化的大小色块,通过巧妙色彩的配合以形成整体的和谐统一,为求色彩的丰富化,注重色彩的相互对比,通过各种不同性质的色彩对比、互相衬托,相互穿擂,以达到色彩互和,神气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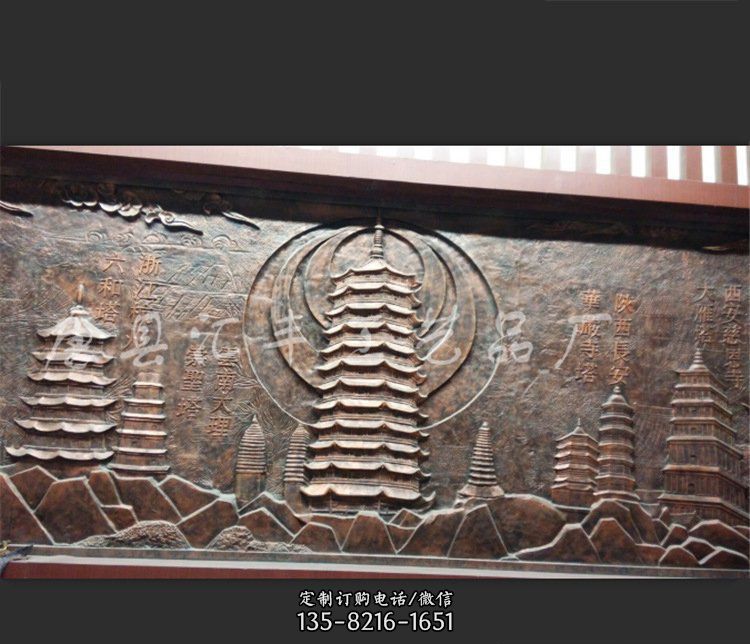
多民族的文化传统、长时期的风格延变,加上绘画材料自身的变化,使敦煌壁画的色彩结构和层次比较复杂。克孜尔石窟建于公元三至四世纪之间,其绘画千法为西域普遍流行的晕染法。所谓晕染法,就是以由深到浅的颜色沿着所绘人物轮廓由外到内的涂抹,使得所绘物体有了明显的立体感和凹凸感,因此中国古代也称之为凹凸画法。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这种凹凸画法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盛行不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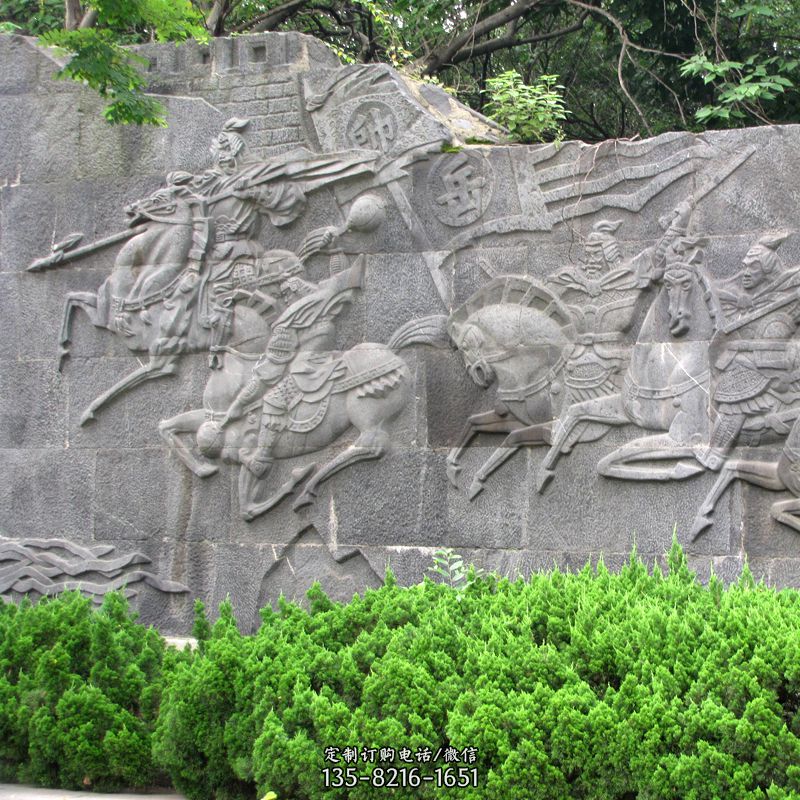
克孜尔壁画从人物形象到构图造型都与古代印度佛教相似,壁画中大量使用色相纯度极高的蓝靛色和石青、石绿等间以土红色、白色。这些颜色经过画师们强劲有力的粗线勾染,使得克孜尔壁画同初期的敦煌壁画相比显得更加粗放朴拙。后期的克孜尔壁画开始出现中原地区的线描技法,整体色彩感觉也更接近敦煌壁画。敦煌壁画虽历经千年,但由于各时代审美观的不同,敦煌壁画的色彩语言也随着时代的不同,其绘画技法、绘画颜料和绘画观念都发生着变化,这种差异大抵以唐朝为分割点。

总体来说,北魏浓郁厚重而有变化,西魏、北周爽朗而清雅,隋唐时代华丽高雅,题材广泛。比如257窟是具有北魏时期壁画特征的典型洞窟,具有早期敦煌艺术壁画的共同特征。该窟以其生动而稚拙的造型、浓烈而深沉的色调,对比强烈的色彩,构成一派和谐温璐的色彩氛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壁画以温和的暖土红为底色.与石育、石绿形成鲜明的冷暖对比,在黑、灰、白色的配合下形成了单纯、明快、浑厚朴实的暖色调。它与主体中心柱佛宪的冷色调又形成了色调氛围的冷暖对比,构成了洞窟色彩整体变化、和谐与平衡。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