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查了下,李昭道的生卒年代是675—758年,而唐玄宗是755年逃往四川的,时间到能对得上,但未免太仓促和牵强了。安史之乱,乱了8年,皇帝仓皇逃窜,宗室多遭杀戮,山河破碎,哪还有心思画这样一幅精工细作的《明皇幸蜀图》呢?所以更有可能是继承“二李将军”传派画家的作品,因为中国历代战乱频发,劫难太多,文物保存太难了,宋以前的画能传下来的九牛一毛都不到,太稀罕了。所以往往就把一些画风符合的无名氏作品,归到了这些画史上著名的大家名下。

前面我讲的《洛神赋》、《步辇图》等都是这样,作者都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却并不影响艺术作品的价值,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窥见这些名家的踪迹,这幅画就是如此,虽然不是李思训或李昭道所作,但是它毕竟是二李将军的画风的存世代表作品,而且年代是很早的。这幅画应该比传为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年代更早,更接近唐画,为什么呢?因为画法上更加高古,早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皴笔,主要是勾线,染色,《江帆楼阁图》里还是有一些皴笔的。从诗里可知,乾隆只是把它当成一幅无款的寻常商客行旅图,他把年代断定为北宋到晚唐之间,还没有想到和唐玄宗逃难联系起来,后来抗战期间故宫国宝南迁,这幅画也在其中,之后就躺在仓库里,一直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才整理出来,那时的名字还叫《春山行旅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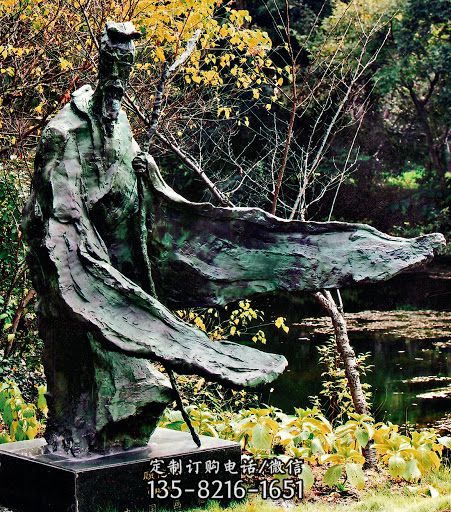
后来有的专家发现古籍中关于《明皇幸蜀图》文字记载:和这幅画中的内容和特征有很多接近之处,后来就命名为了《明皇幸蜀图》,归入了李昭道的名下。这是给皇家脸上贴金的说法,其实唐玄宗是一路逃窜到四川去避乱的,如果叫《唐玄宗跑路图》,其实是更符合史实的。唐玄宗喊着要去御驾亲征,实际上带着杨玉环一家子还有一些亲信,仓皇逃往四川。唐玄宗这时已经72岁了,在西逃路上,一行人狼狈不堪,吃了不少苦。

皇帝跟着难民后面跑,也没有官员接驾,虽然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但换不着粮食,饭都没的吃,没办法连皇帝的御马都杀了充饥。就这样一路狼狈逃窜,还没跑到成都,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兵变,宰相杨国忠被乱刀砍死,唐玄宗不得不赐死了心爱的女人杨玉环。蜀山、蜀道,向来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李白诗里经常屡屡写道,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青绿山水这种画风,特别富有装饰效果,有一种富丽典雅的气质。云白山青,细看,山路水畔还有一些桃李花开放,猛一看还以为是表现春游或者打猎的呢,难怪此画曾定名为“春山行旅图”。

事实上唐玄宗避乱入蜀,是在深秋,秋风萧瑟,形色仓皇,那个画面应该是很衰颓的。所以这一点也成为这幅画到底是不是记载中李思训的《明皇幸蜀图》的一个疑点。不过用二李将军这种金碧山水的画法表现凄清萧瑟的情境还真不容易,太贵气了。崇山峻岭之中有人马在穿行,由远及近,由高到下重重山路隐藏在山岭之间,画中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下方,右下角有一些头戴帷帽的女子们骑马穿行于山间小路,驮负行李的骆驼、腰系弓箭的士卒为其导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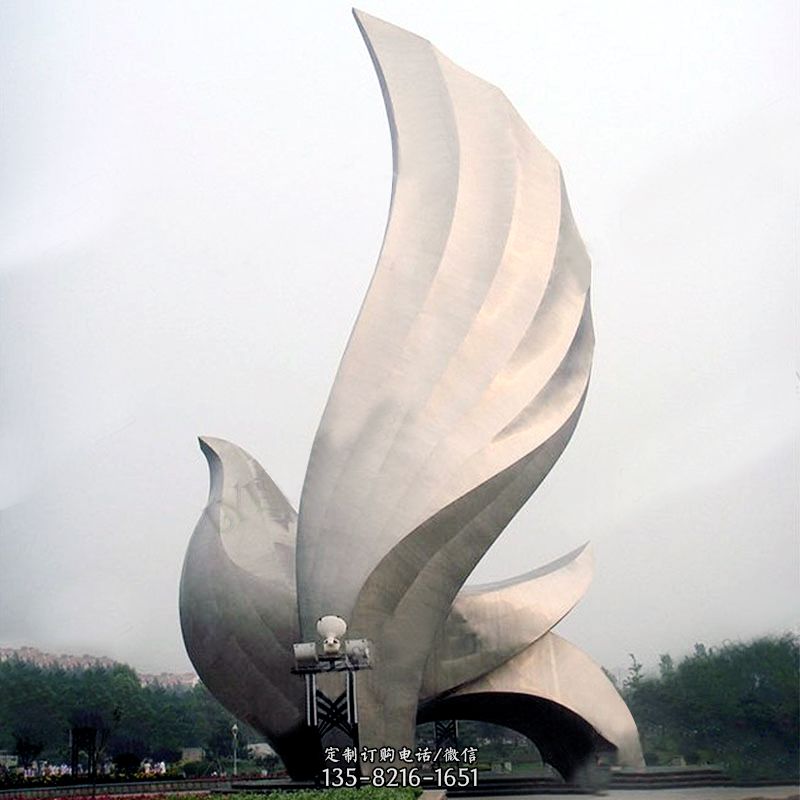
桥的左边,也就是画面中下部,一群挑夫卸下背囊,正在坐地歇息,马卧地打滚,也稍微喘口气。再往前,再过一座小桥,到了画面左下角,一队牵骆驼和骑马的队伍正步履蹒跚地登高。再把视线移到画面左上部,是云雾缭绕的山腰,一队行旅人马从悬空的栈道逆向而来,喻示双方将狭路相逢。皇帝胯下的马的装扮不普通,叫三花马,马鬃梳成三个辫子,故名。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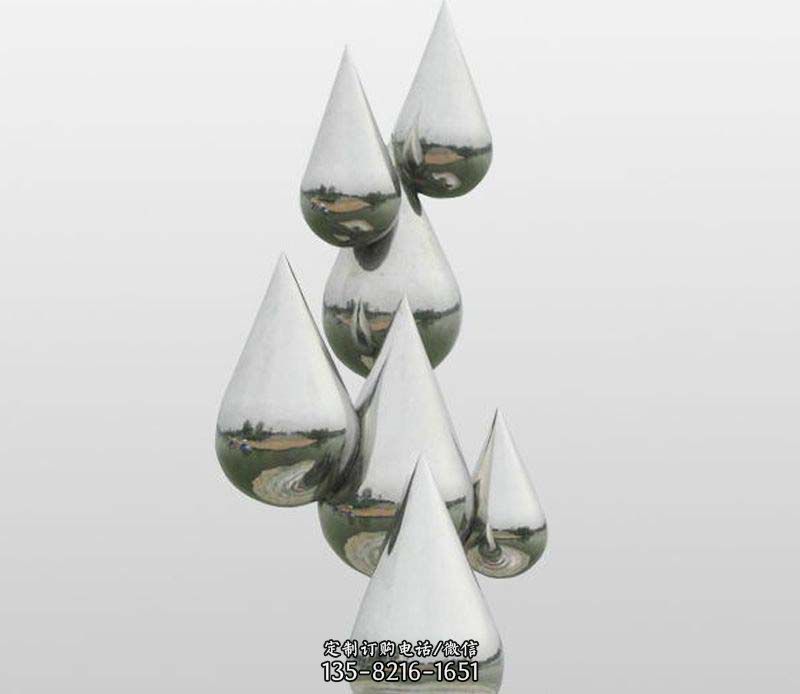
用明皇幸蜀这个主题作画的不止这一幅,后世各个朝代的都有,传世的一共有七幅,有一幅画上唐玄宗后面还有一批三花马,但马上没有人,后人解释是杨贵妃的坐骑,杨贵妃死在马嵬坡了,唐玄宗想念她,还把她的马留在身边。仇英是明四家之一,另外三位是沈周,文征明和唐伯虎,四人中最有名的是唐伯虎,因为他故事多,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老百姓最熟知。

老百姓最不熟悉的是仇英,因为他故事少,专业画工出身,没啥传奇故事,但是他的功夫最好,其他几位都是大文人同时是画家,所以画的都是文人画,修养高但是不太追求画工,论基本功,仇英最好,所以他善于画这些需要表现的非常具体,有人物,有情节,需要非常强的造型能力的这种故事画,《明皇幸蜀图》就属于这种画。在构图上讲更加成熟了,人物与山峦的远近透视关系更加合理。尤其是描绘群山的线条,比李昭道多了几分弹性,少了几分刚硬,显得更加秀雅清丽。

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体”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含蓄蕴藉,色调淡雅清丽,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仇实父欲突过伯驹前矣,虽文太史当避席也,必有信余言者。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若文太史极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前面讲过,金碧山水是李思训在继承展子虔这一路青绿山水的基础上开创的精致富丽的山水画风,成为盛唐时期山水的主流风格,盛极一时。但随着随着唐代中期水墨山水画的兴起,这种古艳的青绿山水画渐渐冷落。

也就是我讲过的“丹青”逐渐被“水墨”所代替了,中国画的主流从装饰性的重彩走向了清新渲淡的水墨风格。这个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有关系,本身中国的老庄思想就崇尚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佛教中禅宗的兴起,也吸取中国道家的“自然”的理念,主张摆脱繁复的外在束缚回到单纯朴素的本性和本质。对文化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山水画的创作观念。禅宗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初祖达摩祖师起,主张直指人心,不拘修行,见性成佛。

五祖之后,分为南北宗,北宗神秀是以“坐禅观定法“为依归,渐进禅法,渐修菩提。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画从中晚唐开始萌芽,文人画也叫“士大夫写意画”,是追求一种游心物外,不拘泥工整与形似,也不讲目的与价值;总之从中晚唐以后中国画的走向就改变了,对绘画和画家的评判标准也改变了,唐以后最重要的画家,在历史上地位最高的画家都是文人画家,对于他们,画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人的修养和精神境界成为最重要的了。
在这个历史潮流之上,明代大画家董其昌,以禅喻画,根据佛教的南北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绘画上的“南北宗论”。他将唐代至元代的绘画发展,按画家的身份、画法、风格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是文人之画,而北宗是行家画,崇南贬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把王维定为南宗的的始祖,在董其昌看来,南宗画是文人画,近似南宗禅;具体说来,南宗画是以淡、净、雅见长的水墨画、山水画。而北宗画是指画风刚性的、躁动的、雄浑的、气势豪纵的,画法上使用勾线填色斧劈之法的这类画。
认为北宗的山水画,精工之极”,皆“其术甚苦”,属于“习者之流”。他还把南北宗的画家和寿命联系起来,认为“南宗”画家能够长寿,“北宗”一系的画家短寿。因之作画不但不能损害精神、消耗精力,还要十分轻松,“其术亦近苦矣”的“精工”之画即不能学,要学就要“一超直入如来地”。要知道董其昌的影响多大啊,清朝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是他的粉丝,学他的字,学他的画,清朝三百年的书画都受他的影响。
所以他这个理论影响太大,以至于李思训这一路精工细作的青绿山水画风,和“匠气,行画”“短命”联系到一起了,更加式微,除了画匠和民间老百姓喜欢,文人基本就不碰了。这个理论把中国画提到一个哲学高度,有一定贡献,但也有点牵强附会,流弊也是很大的,艺术和审美应该多元化的,不应该是一种标准。这个理论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中国画不重技法,空谈境界的毛病。晚唐已降,李思训一路金碧山水的画风逐渐沉寂,但其余波绵延,在北宋后期画坛的“复古”潮中,画家们将水墨山水的精湛的“勾、皴、擦、点、染”的笔墨技法融入其中,创造出既艳丽而又脱俗的臻于完美的青绿山水,其中以青绿为重的谓之“大青绿山水”,代表作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也有作浅绛淡彩之后薄敷青绿石色的,谓之“小青绿山水”,如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等,都在画史上留下惊艳的一笔。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