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前,凭借多年自学积累的雕刻技艺,他成功入选国家“一号工程”千手观音的修复团队,正式成为一名石刻修复工作者;近年来,不忍石刻风化,他又决心复制雕刻大足石刻龛窟造像。一锤一凿之间,他用双手“守护”石刻,一如千年前那般光彩、耀眼…他就是彭柳升,大足石刻研究院一名普通的石刻修复人员,因为热爱,他不断自学钻研,从保安跨界成为“石刻医生”。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实验室的一角,摆放着几个半人高的菩萨造像,这些造像均按照大足石刻经典龛窟圆觉洞造像复制雕刻而成。

“以前守石刻,后来修石刻,到现在复制雕刻石刻,我希望把大足石刻保护和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感受大足石刻的魅力。1990年,18岁的彭柳升离开家乡湖南长沙,来到大足成为一名武警战士。喜欢绘画的他,一到休假时间,就爱去文化馆看人家画画。1996年年末,广大寺出现文物被盗的情况,大足石刻研究院随即成立了由彭柳升等三人组成的安保组,开展夜间侦查守护工作。眼看情况紧急,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和穷凶极恶的盗贼,彭柳升和两名同事迅速上前,经过一番激烈搏斗之后,他们成功将两名偷盗者移交给公安机关。“我记得,来景区写生的团队很多,有画画的,也有雕塑的。

”彭柳升心想,那么多人专程过来学习,而自己每天都在这里,天天都对着石刻,有那么好的学习机会,为什么自己不学着雕刻看看呢?“第一个作品是一个吊坠,是照着大足石刻里面荷花童子的形象雕刻的。”一个星期后,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石雕作品,朋友看后,认为他很有天赋。对于没有专门学习过雕刻的他而言,宝顶山大佛湾石刻就是天然的“学堂”。

夜间值班巡查时,山湾里一片寂静,彭柳升举着手电筒,一边查看石刻造像的完整性,一边在心里勾勒出每个造像的轮廓和造型。有时看着看着,自然而然就明白造像的鼻子或是手臂的曲线应该怎么雕刻了。彭柳升对雕刻十分着迷,他甚至将雕刻工具和石头放进衣兜里,一到下班的时间,他就拿出来雕刻。在他的坚持下,雕刻技艺突飞猛进,有人还找上门购买他的作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开始前期勘察研究,负责现场安保的彭柳升第一次发现千手观音病害如此严重,意识到石刻修复刻不容缓,对石刻修复工作心生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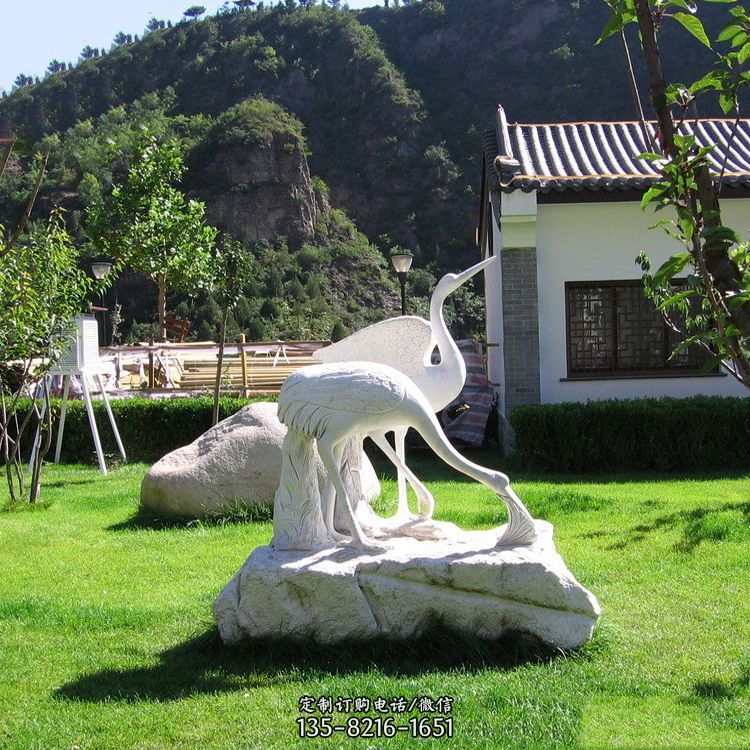
2011年,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启动,由于修复人员的缺乏,单位内部开始征集人员加入修复工作,彭柳升主动提出申请。但想要真正成为修复团队的一员并非易事,除了要求通过石质文物修复培训外,彭柳升打听到,修复工作要长期接触大漆,必须得通过大漆过敏测试。于是,在未正式进行过敏测试前,彭柳升事先给自己来了一场“预考”。他托人要了一些大漆,晚上回到家偷偷地涂抹在自己的手臂上,第二天确认没有过敏才放心。

在长达5年的修复时间里,他主要负责千手观音手部的修复工作。这是千手观音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缺,当时现存手掌及掌中红布帕为后人用水泥补塑,是一只“假手”。修复团队四处寻找修复依据无果,于是提出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的“新手”。为此,彭柳升和同事利用这只手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反复进行了几十次的虚拟修复和精雕油泥模拟修复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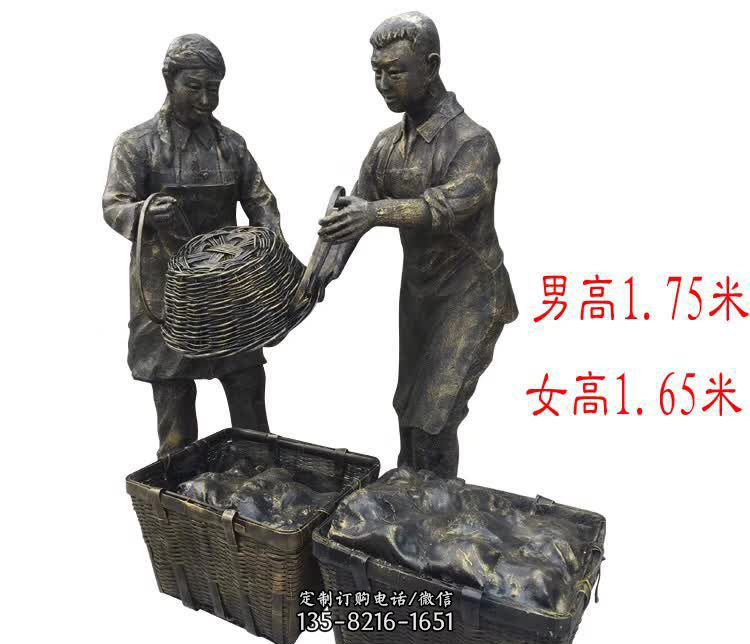
最终,他们成功完成这只关键手臂的修复,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他利用雕刻技艺和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取材大足本地石材,采用平面线刻、浮雕与立体圆雕的形式,复制雕刻大足石刻风化较严重的重要龛窟,包括千手观音造像、圆觉洞造像全窟、六道轮回、卧佛、吹笛女、北山媚态观音等,涉及10多个龛窟,数十尊造像。“这是部分圆觉洞的菩萨造像,总共12尊,这里摆不下了。”顺着彭柳升手指的方向,摆放着几尊造型各异的菩萨造像,个个风姿飘逸,身上的袈裟舒展柔和,细节处也与圆觉洞造像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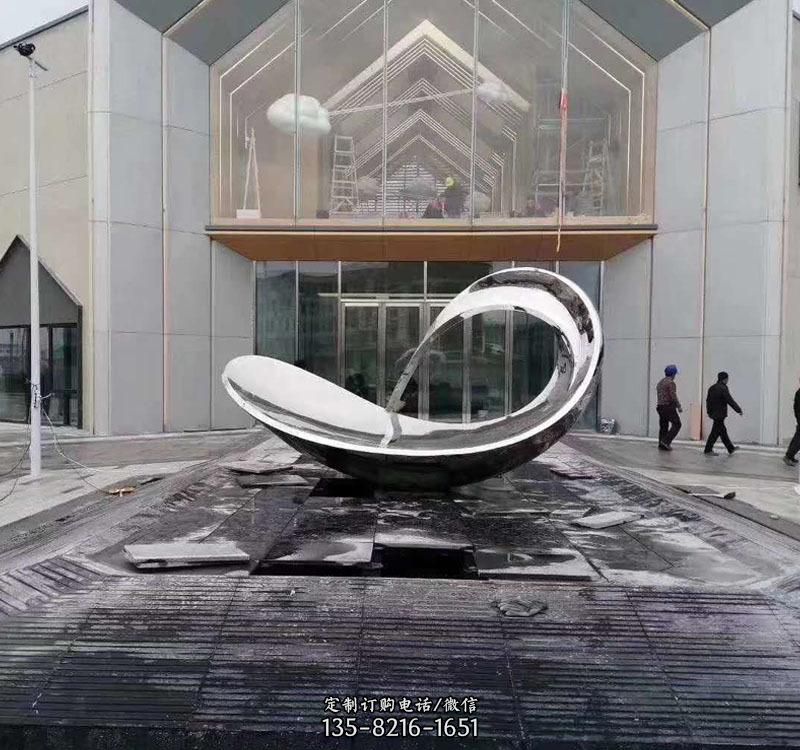
闲暇之余,彭柳升还创作了不少以大足石刻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比赛中屡次获奖,他个人先后被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重庆市优秀民间工艺家、重庆市民间工艺大师,多次接受国内外记者采访报道,让更多人了解到大足石刻。“无论是复制雕刻还是创新作品,都是对石刻的保护和传承,为大足石刻赋予新的活力。”彭柳升说,“大足石刻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保护和传承下去。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