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欧美各国的雕塑公园中有种特殊的类型称为“”,笔者将其译为“雕塑之径”。其中的雕塑发展了一种独特的、自然与艺术和谐共生的关系,成为当代西方雕塑创作中一种极具生命力与个性的类型。“雕塑之径”源于英国大湖地区的“格瑞泽戴尔艺术项目”,这一项目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8年由比尔·格兰特创办的格瑞泽戴尔社团。他们最初关注的焦点主要在表演艺术方面,直到1977年才开始雕塑创作活动,并逐渐扩大规模。此外还有“波特兰雕塑&采石场联合企业”、“基尔德水面和森林雕塑公园”、“古德伍德雕塑”等虽然没有完全照搬“格瑞泽戴尔艺术项目”那种雕塑与森林相结合的方式,但实质仍然是在延续该项目衍生出来的某些观念,也特意强调雕塑创作与当地历史文化、地形地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既然不列颠君王可以是美少女。

美国也有个别雕塑之径的创作案例,如1999年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奇克伍德植物园艺术博物馆的卡雷尔林地雕塑之径。但雕塑公园在美国更多是以大型的旷野雕塑公园与小型的博物馆雕塑花园的方式出现〔1〕,欧洲大陆地区也没有广泛发展“雕塑之径”的例子,这说明“雕塑之径”一般可被看作是在英国首创并发展起来的雕塑创作形式。那里的森林、高地幽深清冷,植被密集、潮湿,确实具备开辟“雕塑之径”的独特地形优势。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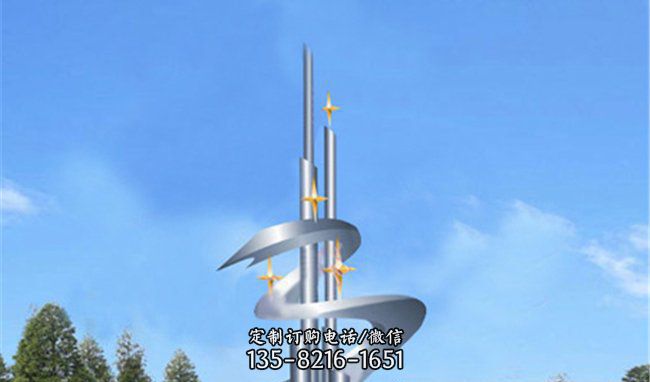
美国的大型雕塑公园以草坪为主,看看纽约风暴国王艺术中心就明白了,整个公园的地面像是一张一目了然的绿色巨毯,有时在雕塑之间是根本看不见道路的,你可以骑自行车甚至开车踏草地一路追逐那些大型雕塑的身影。英国的“雕塑之径”则不然,它其实是一条条穿插于密林间的步道,凭靠着大片森林为依托。大湖地区的格瑞泽戴尔森林占地面积达8700英亩,雕塑“隐藏”在迂回曲折的林间小路中,游人在茂密的森林中不能随意行走,只能按图索骥,沿着小径寻找雕塑的踪迹。而在爱尔兰的林地雕塑公园,连导览的手册也没有印上地图,发现林间雕塑的过程变成了一项令人着迷的“寻宝活动”。巨大的几何形这种风格出现在代的不列颠。

雕塑依存的自然生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创作审美追求的不同。大型雕塑公园的疆域中也可以有大片树林,但树木一般作为雕塑的背景出现。远眺林前、草地上那些壮硕的雕塑,以高大的身姿,靓丽的色彩炫耀着活泼的性格。而格瑞泽戴尔遮天蔽日的森林中,雕塑就生活在树木的身旁,它们或依偎在林荫之侧,或匍匐在杂草的地面,或悬垂于树枝之下,把粗壮的树干当作它的支撑体。如不列颠裔的美国制造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汽船发明家富尔顿。

高大的树冠和茂密的树枝遮挡住天空,使雕塑几乎无法接触到灿烂阳光和急劲的野风。森林代替草地体现出了不可逆转的优势,大型雕塑公园中的作品如果挪到这里,一定会感到强烈的“水土不服”:苏维罗的“钢铁巨人”根本无法放到树林中间,考尔德的活动雕塑在密不透风的包围中也完全失去了特色,斯内尔森的“闪光雕塑”在这里也会魅力全无。雕塑家必须根据“小径”的特点来创造,雕塑和森林不可逃避的迫近感强迫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里的雕塑几乎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们和树木、小溪合体,要不然就隐蔽在黑暗而青葱的森林中。接下来讲讲不列颠吧青铜棱纹盾牌。

绿草如茵的大型雕塑公园带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而幽暗的森林则容易使人感到压抑,心怀郁结,体验到人类生活的艰辛,因此“雕塑之径”似乎表现出了对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关怀。这里的雕塑不是貌合神离地模仿自然物的外表,也不像草坪雕塑那样“浓妆艳抹”和“高高在上”,而是在潜隐于自然的过程中使历史的变迁得到显现。雕塑家离开了工作室,远离城市的喧闹,需亲手完成自己的作品,辛苦的劳动使他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而此时此刻,静默的森林早已变成人类改造自然的精神积淀。森林中的树木是烧炭的原料,这里到处保留着烧炭工人留下的印记;最后辗转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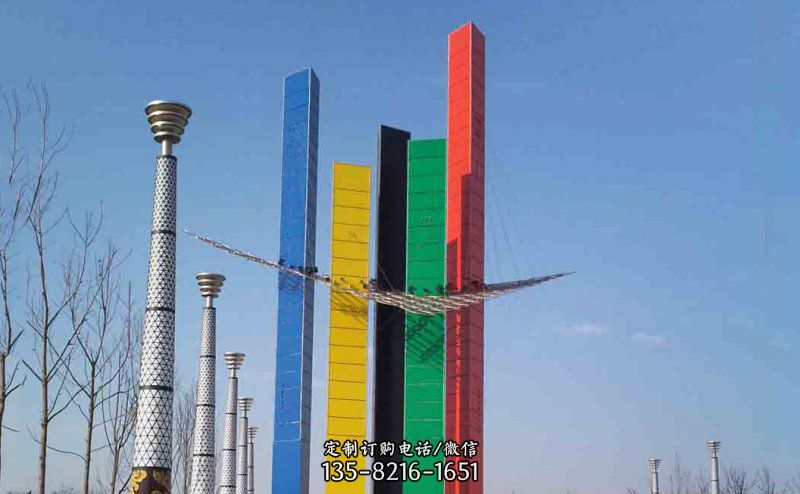
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矿,曾源源不断供给人们取暖,林中炼铁炉剩下的废铁业已成为工业时代来临的印证;还有森林中居住的各种生命,茂盛的植物、流浪的野鹿、盘旋的老鹰…雕塑家们在这里创作,仿佛使自己游荡在自然与历史中间,他们用雕塑的语言把这些感悟表达出来,这正是“雕塑之径”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妨以英国的“迪恩雕塑之径”,及其近邻爱尔兰的“林地雕塑公园”为例,领略“雕塑之径”这一创作形式的奥秘与真谛。一些加拿大名校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西蒙菲沙大学等都将在今年开设一些全新课程和新专业。

在格洛斯特郡西南12公里处有片皇家密林,它的名字叫迪恩——是英格兰最古老的橡树森林,早在1939年就被辟为了国家公园。事实上,这片林子也确实凭借它的神秘气息与绝世美景启发了作家们的灵感。且不说这里是英国作家J.R.R.托尔金《指环王》系列中精灵居住的森林原型,就连风靡世界的《哈利·波特》系列中妙不可言的魔法世界也充斥着这里的影子。小说作者J.K.罗琳幼年时曾生活于此,也正是这里的草木点燃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激情。躲在韦斯莱家“陋居”地下搞怪的地精、藏身在树丛中的家养小精灵和奇珍异兽、海格教授简陋朴实的木头屋子…不列颠的殖民统治者蛮横地砸碎了印度人的手工纺织机。

就连系列丛书的终结本《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哈利一行人历经磨难从魔法部盗走魂器后下意识“幻影移形”到的地方也正是迪恩森林。迪恩森林曾是英国皇家狩猎场,是受人为破坏最小的森林保护区,拥有着种类繁多、不胜枚举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生长于斯的橡树更是被用来制造拿破仑时代和都铎王朝时期军舰的“御用”材料。橡树根系发达、树枝粗壮、生命力旺盛,无需悉心栽培,即可自行生长成材,除了可以用之打造坚不可摧的军舰之外,同样是整个西方文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树种。并形象地称不列颠皇家马车为浓缩英国千年史的时间胶囊。

这里的山毛榉和欧洲栗也很常见,秋天来临之际整个林场泛起由黄至红的渐变色波浪,耀眼夺目、美轮美奂,著名的世界旅游杂志《孤独星球》把这里列为了全球十大欣赏美丽秋景的最佳地点。1982年,西部港口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的创始人——杰瑞米·里斯最先提出了打造“雕塑之径”的构想,这可能与他曾从事林业工作的背景有关。此后“迪恩雕塑之径”在他与策展人罗伯特·马丁,以及同样具有林业背景的马丁·奥勒姆的不懈努力下逐渐成型。放置雕塑的区域原是一段长约3.5英里的环形道路,堪称英格兰最古老的步道之一,现在在艺术家的奇思妙想之下,变成了雕塑展示的理想环境,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形态。不列颠尼亚皇家马车被放置在白金汉宫的皇家马厩。

穿行整条步道大约需要三小时路程,沿途经过约二十座雕塑,虽然偌大的森林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但观众只要耐心地围绕既定区域行走,不难找到那些躲藏在步道附近的雕塑。小路曲曲折折,磕磕绊绊,随着时间的绵延、空间的变幻雕塑逐渐显露在观众面前,那不经意的邂逅,随时触动起观者的万千思绪,为欣赏的过程增添了神秘与浪漫的质感,营造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迪恩雕塑之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一组组经典杰作,成为英国最具魅力的雕塑公园之一。大自然以巧妙而迷人的方式与艺术互动,作品的选址更强化了技术与风格的多样性。虽然个别雕塑已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多数作品仍得到了妥善保管,别看这里表面上一派清幽气象,实则云集了世界各国的雕塑大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洞实验室内。
大卫·纳什1945年出生于英国南部,除了是杰出的雕塑家、地景艺术家之外,还拥有着许多头衔:采用自然中有生命力的材料,并在其中应用永恒的象征符号是他惯用的艺术语言。锥体、球体、立方体等象征性的形式经由其手诞生、成长,继而转化成有关自然与生命的复杂主题。《黑色圆屋顶》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横亘在眼前的是一个黝黑的圆形突起形状,和长满蕨类植物的地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仔细观察,原来这个其貌不扬的“黑色的圆形”是由900块锥形的松木焦炭堆积而成的,寂静地匍匐在那里,好像是古人的坟墓。虽然拿北欧和不列颠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和法国铁器时代的青铜器来对比虽然有些偏驳。
它们的存在有效地加强了作品对选址地的认同感,并且彰显了自然力特有的审美属性。不同于那些追求永恒的经典杰作,作为终将回归自然的雕塑作品,它会随时间推移走完自己既定的宿命,顺应循环之规律,维护自然秩序之威严。他在格瑞泽戴尔森林创作过一件同名作品,纳什是这样回忆其创作过程的:“1978年,我曾在坎布里亚郡的格瑞泽戴尔森林工作,经常看到具有百年历史的烧炭遗址在地面留下的圆形空间,从山坡经过,刚好辨认出它们的模样…从属于罗兹的不列颠南非公司在当时控制了广袤的土地。
这些痕迹虽然难以辨认,但它显现出人的活动,烧炭浓缩着一种在场的感觉,它令我印象深刻。”〔3〕德国女艺术家玛格达莱娜·耶特洛娃的作品《地点》直接使用了森林中最常见的粗壮枝干,用最基本的交叉结构表现出了一种原始的多意形象,并且从本质的高度上还原了森林的历史。如果你是从坎诺普山谷来仰望这件作品,那原始的崇高感足以令人虔心敬畏,它盘踞在小山丘上,如同国王的宝座。远远望去,又像一位首领在俯瞰自己的领地,或者是童话王国中刀枪不入的怪兽。再换个角度观望,又会使人联想到史前的石栏,仿佛冥冥中已经在那里伫立了千年万年。那么不列颠尼亚皇家马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吉姆费克林顿的私心。
“迪恩雕塑之径”有一类使用“悬浮”手法创作的作品,颇能体现森林与雕塑结合的特点,雕塑不是通常那样矗立在地面,而是直接将树木的枝干作为支撑体。彼得·阿普尔顿创作的《梅丽莎的秋千》是一个悬浮着的声音装置,名字取自雕塑家的女儿。科妮莉亚·帕克1986年创作的作品《吊火》,那火焰般成捆的金属悬挂于枝干的上方,从远处看犹如一顶加冕用的皇冠,阳光直射时,皇冠又化为了熊熊燃烧的火炬,连带着下面的树枝也仿佛在炙热的熏烤中劈啪作响。凯尔·史密斯的一件名为《铁路》的作品也唤起了人们对这个地区过去工业活动的追忆。不列颠的雄狮去了美国国会。
他在作品中挪用了某片区域中一段废弃铁路道线中的20根桉树枕木,并且通过雕刻的方式使废旧的轨道变成了一种诗意的表达,让森林的前世与今生在此交汇,艺术家在这里化身成为“时光的使者”,将你的注意力导引向那未曾谋面的神秘历史。走完了“铁路”,也许你想试试上一段“楼梯”,布鲁斯·艾伦创作于1986年的作品《天文台》将成全你的想法。这件作品位于一条小溪的前上方,他不但为你铺设了一段上升的楼梯,还打造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我觉得铁器时代出土的青铜盾牌才是最能代表不列颠当地青铜工匠制作水平的。
当你满怀好奇爬上这段阶梯,却发现仅仅只是瞥见了一个“不自然”的池塘,外表看上去更像一个漏水的船头或是一个沉下去的深洞。但正是这样一个装置却实现了现实与过去之间的时空转换,使自然重新变回了昔日的矿场。也许你不曾真的读懂艾伦蕴藏在这件作品中的哲学思考,也不必太较真儿,这件作品旁边恰好挨着一个简单活泼的可爱家伙——英国女雕塑家索菲亚·莱德创作的《小鹿》,用茅草编织的作品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手法,它完全摒弃了深刻的寓意,仿佛刚从大地与树根的缝隙之间钻出来一样,已经完全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之中。又名不列颠尼亚皇家马车。
生于1925年的伊恩·汉密尔顿·芬利身兼诗人与艺术家身份,曾创作了苏格兰最具野心的永久装置作品《小斯巴达》,被誉为“20世纪苏格兰最重要艺术家之一”。他习惯用古典铭文阐述、雕刻,再加上令人不安的典故来表现战争幻想和暴力美学,许多作品被奉为概念艺术的杰作。在“迪恩雕塑之径”中,他致力于把用不同语言雕刻的石质徽章铭文应用到其作品《寂静之林》的树木之中去,为守卫森林的“卫士”们树碑立传。彼得·兰德尔·佩奇那硕大的《松果与容器》是围绕一棵苏格兰松和一棵橡树创作而来的,为的是提请人们注意自然界中存在的那些微小易碎的东西,而他对松果和橡子的复杂诠释恰好位于它们各自的树下。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率军入侵不列颠。
与《松果与容器》同样显眼的是凯文·阿瑟顿安置在林中小径一侧树冠之上的玻璃花窗作品,它在灰暗的森林背景中折射出流光四溢的色彩,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为重叠茂密的树冠披上了瑰丽的霞帔,绚烂之极,颇为浪漫。艺术家们的想象力似乎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发挥,雕刻而成的松果、橡子杯已经见怪不怪。通过观念的介入,埃里卡·谈甚至铸造了青铜竹子,将这种非本地的物种引入森林,看上去像是一段消失文明创造的史前造物。艺术家的创作动力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在作祟,有时或许是为了表达对逝去之物的追忆和眷恋。特朗普心仪的不列颠尼亚皇家马车也是出自他手。
在英格玛·塔利亚创作于2002年的作品《生命周期》中的鸟窝已经被人为捣毁破坏了,但当地人又放上了原来的照片,并且被很好地保护起来,这般做法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对象与自然融合的观念,而是提升了雕塑公园存在的社会意义。在另一个象征性的雕塑创作中,卡罗尔·德雷克在森林地表之下埋藏了五块钢板。钢板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他用原始的林间泥土将其掩埋,其效果是向人们展示大自然的伟大之处——它是用这样的方式俘虏、埋没人类的文明并将之盖棺定论。与伊丽莎白二世同乘不列颠尼亚皇家马车下榻白金汉宫。
“迪恩雕塑之径”中形形色色、极富创意思想的大型创作还有很多。迈尔斯·戴维斯的《住宅》建在森林中,看上去像是一个倒错的矿井,不是向下钻研,反而向上生长。住宅通常代表家庭的形像,但这个住宅却暗指工业,并且从中偶然发出的金属铿锵声很容易使观众迷失方向。内维尔·加比在作品《未经加工》中成功玩转了本地的特色守护神——橡树,从对原木的挪用、切割到对地表的挖掘,以及形体的拼接,他在这件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由拿破仑时代“海军橡树”所启发的灵感。
加比选择茂盛森林中的一棵橡树并将其砍伐,所造成的缺失感仿佛是给天幕上开了一个口子。他从橡树生长的地方向下挖掘,形成一个空洞,让人联想到一棵参天大树所耗的巨大水量,接着他准备用橡木做一个完美的立方体,亲手将木材切成一个个小块,再把它们组装成一个实心堆块,使之呈现出后极简主义拼板玩具的视觉效果。“迪恩雕塑之径”并没有向以往的创作项目那样十分重视雕塑的长久保护,雕塑在森林中生活的挑战就是体验到物质转化的力量,循环、分解的全程。
这一做法与“大地艺术”中的某些观念十分相似,这一流派的艺术家认为艺术、人生都是短暂的,使作品消解的能量同样不受艺术家的操控,作品完全取之于自然,归之自然。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地艺术”是大地本身变成了一种造型语言,而“雕塑作品”始终是一种独立于地面的造型或结构,也不一定像大地艺术那样追求移山填海般的宏大效果。大卫·肯普的《绿色的捕鸟人》刻画了一个神秘的捕鸟人,是用树木的残枝和森林中拾来的碎片拼凑而成的,它看上去瘦弱不堪的身躯早已抵抗不住疾风骤雨的袭击,仿佛顷刻间便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分崩离析。
肯普坚定地认为,这件作品“将随时间而消失,显现出遭人抛弃的心酸”。〔4〕雕塑将显现自然物质转化的观念已在驻扎于“雕塑之径”的艺术家那里达成了共识。纳什在创作《黑色的圆屋顶》时也意识到雕塑的形态将随着季节而变化,并最终遗憾地消逝于它们曾经依恋的风景之中:“我坦然面对雕塑终将消逝的事实,霉菌侵蚀,变质,植物生长加速了它从小圆堆变为残骸的过程。我不让客体对抗自然的因素,反而努力使它们介入雕塑,使其在环境中显示出不断变化的迹象…
最近的观察中我已发现了作品外形的变化,体验自然和雕塑的相互融合是一种十分有趣的过程。”〔5〕爱尔兰的林地雕塑公园同样是一个以森林为载体的创作项目,它位于都柏林南部大约20英里处的威克洛郡,所处地点是一片600英亩,原名“魔鬼谷”的茂密森林,这里位于欧洲的边缘地带,因此保持着更加野性与静谧的气息,当地的媒体也习惯称之为本地的“秘密画廊”。公园外围是一片绿波起伏的爱尔兰村落,景致美丽非凡,可以媲美旅游手册中过的宣传图片。
入口的位置十分隐秘,如果不仔细观察就会错过,当你猝不及防地听到游客发出的惊叹,那一定是他们不经意间发现了隐藏在林地间的雕塑。森林的所有人和管理者是一个负责爱尔兰林业事务的半国家性质的机构。1994年,从公园创建之初开始雕塑创作的时候,就始终贯彻了两个基本理念,即“加深对木材的认识,使之成为艺术与功能的媒介”和“通过雕塑的手段建立关于木材使用的文化”。因此这里的雕塑创作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意义与主题,使用的材料全部来自身边的森林,作品风格也完全融于自然,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和谐关系。
按照前任行政官恰拉·京的回忆,“这一理念是前任林业顾问马丁·谢尔登和多纳尔·马涅的创意。他们认为这将成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因为它围绕着木材,并且融合了艺术、社会和问题”。〔6〕从1999年开始,林地雕塑公园每年邀请一名爱尔兰籍艺术家、一名国际艺术家,以及一名通过公开竞争推选出来的艺术家到此进行创作。“这里的一切都是安全的,因为这里是一座公共的雕塑公园——举例来说,这里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伤人的锋利的边缘。
我们不想限制艺术家的自由,但作品需由木材制成,有一定的耐久性,能保存10年以上。我们不寻找暂时性的作品,因为我们要让它们扎根于大地。”〔7〕目前,这里已拥有了爱尔兰、英国、法国、葡萄牙、拉脱维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雕塑家创作的18件作品,大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木料特有的材质特性,经过艺术家的妙手略加雕琢,便形成一种浑然天成的朴素之美。在魔鬼峡谷入口处的侧面,你会看到两条弯曲的柱状物,是爱尔兰雕塑家米歇尔·沃伦创作的《安泰》。
安泰是希腊神话中一个巨人的名字,只要身体和大地相连,它就是无可匹敌的。作品的材质是杨树和落叶松木,它的形式呈现出如“生理弯曲”一般的姿态,突出并强调了周围树木的垂直效果,沃伦用单纯而简率的雕刻手法,暗示出树木和土地之间的联系。在一条通往停车场的一英里的小径旁,放置着1996年由墨西哥雕塑家若热·迪·邦创作的无名作品。它的形式感极强,从悬崖上突出,躯干上挺,指向远方,像一架延伸出去的望远镜,或者更像瞄准远方直射的一门大炮。一棵死去的树木无法永远保持鲜活的生机,但它将在这里以“哨兵”和“守卫者”的姿态获得新生,可以将这件作品的涵义理解为“森林卫士的自我守护”。
在它对面是莫里斯·麦克唐纳1996年创作的《圆》,这件作品表现的内容与树的体块、密度和重力有关,“圆”由大量烧焦的小圆柱组成,象征着云杉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无数同心圆结构。作品的创作遵循了树木成材的过程,强调了对树的物质属性与自然力的探索,以及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深刻体验。继续沿停车场以及邻近的野餐区行走,会看见另外两件就地取材且原始意味浓厚的作品。雅克·博塞尔的《查戈》创作于1997年,是一件由欧洲落叶松木制成的415厘米高的矩形雕塑,象征非洲的火神。
他这样形容这位神灵“他出现了,然后离开了那巨大的焦黑且被烧坏的树干。为了安抚神灵,当地人在他们的祭品中插入金属,并诚心祈祷”。〔8〕不远处还有英国雕塑家德雷克·维蒂奇创作的《英镑》,由16个刻有纹饰的有机形柱组成,看上去像中国武侠小说中供人练武用的“梅花桩”,貌似零散分布,实则浑然天成,自成阵法。“英镑”这个单词本身有重量、货币价值、安全区与力量的含义,作品以“英镑”命名是为了表达“空间的价值以及对我们所处环境的评价”。
沿着隐蔽的小径前行,便会见到奥米·塞奇1996年创作的《无题》。这件作品从表面上让我们联想到机器般的刚硬冰冷,那带有暗喻性质的矩形长板向外延伸着,像打出了一个暗示性的手势。“这件作品就地取材,结合了此地堆积的不同重量和密度的木材。我想借此把不同事物之间的组合与平衡用视觉的形象表现出来。”〔9〕卡陶·布赖恩的《七座神殿》同样创作于1996年。
与其说是定点雕塑作品,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片原始遗迹。它们的存在是用以祭奠爱尔兰大饥荒后出生的七代人的亡灵。如果你在深夜与之相遇,神殿看起来就会莫名诡异,那些树木枝干的拂动姿态和人的躯干异常相似,这种树木和人类之间的潜在联系使得夜晚的森林充斥着诡谲与神秘的气息。上文只是简略浏览了欧洲雕塑之径中的两个案例,雕塑之径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首次出现或许只是源于个别艺术家的奇思妙想,但至今它已经在英国与邻近的不列颠群岛国家中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创作形态。与常见的草坪雕塑公园相比,它的特点是以阴翳、幽闭的森林为背景,以蜿蜒崎岖的小径作为线索展开雕塑的创作与欣赏活动。
由于进一步结合了森林的环境特色,雕塑之径的创作无论在造型上、色彩与材料的选择上都更加突出了作品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相互融合的关系,在作品的整体意蕴上更体现出一种神秘与忧郁的性格。在雕塑的思想内涵上,雕塑之径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更加深刻的反思精神,正如在迪恩雕塑之径和爱尔兰林地雕塑公园中的作品那样,或包含着对自然力量的崇敬,对工业活动的诘问,对人类历史的反省,对原始文明的眷恋…
毕竟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切,对人类未来出路的探寻已成为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雕塑之径不但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创作形态,更为西方雕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与“雕塑公园”这一范畴相对应的英文词汇主要有“”“”两种。前者可以译为“雕塑花园”,这词组强调在“房前屋后”之类的小花园中摆放雕塑,它们通常建在建筑物四周或附近,作为室内雕塑展示空间的扩充,一般面积较小,大多在几英亩。
一是有许多博物馆会利用周围的庭院摆放较大的雕塑,例如美国华盛顿赫什豪博物馆雕塑花园;二是在一些著名雕塑家的工作室四周通常也会放置他们创作的大型作品,这些场所会逐渐对公众开放,例如英国的亨利·摩尔基金会雕塑花园、巴巴拉·海普沃斯博物馆和雕塑花园。后者可以译为“雕塑公园”,这一词组强调将更大型的雕塑“停放”在广阔的自然空间中,是一种强调雕塑与自然生态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展示场所。这些公园通常远离都市,建在郊外或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有些面积甚至达到了几百英亩以上,例如纽约风暴国王艺术中心、美国俄亥俄州的金字塔山雕塑公园。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