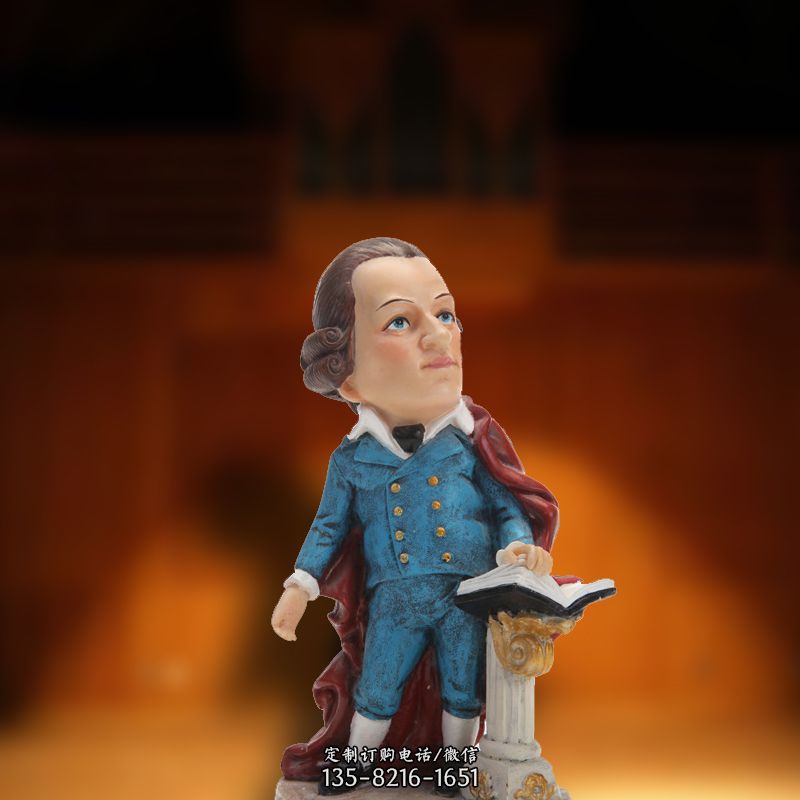
他们是生于18世纪的旷世奇才莫扎特,以及相隔152年后出生的指挥大师卡拉扬。这里还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音乐之声》的拍摄地,而这部电影的原型——二战期间爱国将领冯·特拉普上校一家,就生活在萨尔茨堡。把这三者奇妙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全球范围负有盛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在每年的七八月间点燃全城火热的音乐情怀。这座在奥地利原本排名第四的城市,因为与音乐有关的这一切而享誉世界。莫扎特创始人安德鲁米尔本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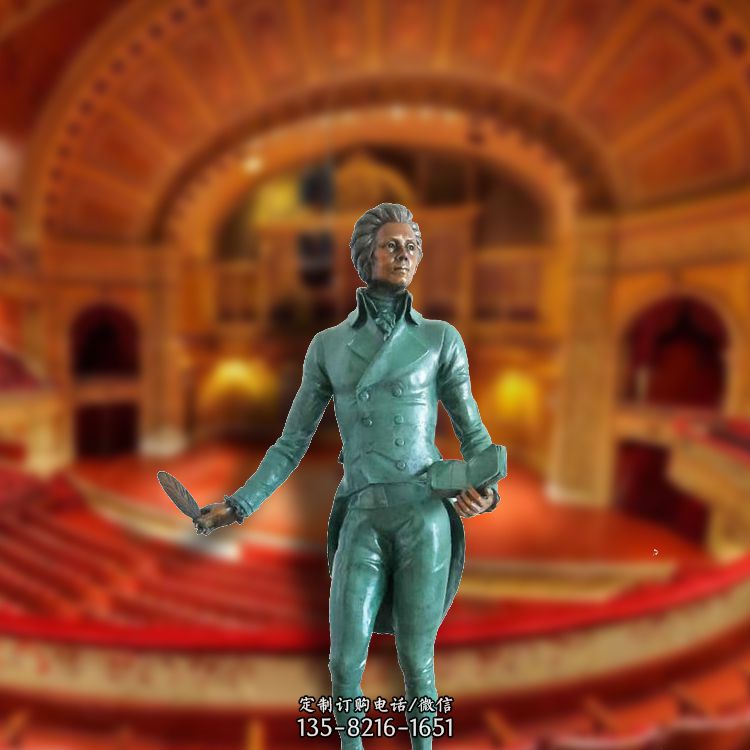
相信进入萨尔茨堡的每一位旅行者,都会被如影随形的莫扎特氛围所感染。以莫扎特命名的巧克力店、礼品店、唱片店、剧院、学校、咖啡馆、广场、饭店等无处不在。莫扎特的头像被印在巧克力盒、巧克力球上、冰箱贴上、徽章上、服饰上、招牌上、会唱歌的小提琴上,更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位音乐爱好者的心上。莫扎特的故居坐落在萨尔茨堡粮食大街9号,普通的街道,不是很宽,那座被柔光笼罩的金黄色6层小楼也并不很显眼,险些被我们走过了。这种亲和力来自于莫扎特为了创作音乐的纯真心态。
还好,当时正巧有一群“莫粉”聚集到那个门口,热烈的交流声把我们召唤了回来。著名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就诞生在这里,因此又被称为“费加罗之家”。因为没有中文导览,我们英文又不娴熟,所以只能大略浏览。据说馆内珍藏了一缕莫扎特的金色头发,可惜没有瞻仰到,过后不免有些遗憾。小小莫扎特天赋异禀,从6岁到16岁之间的10年时光,经常被身为宫廷乐师的父亲安排和姐姐赴欧洲各地“演奏旅行”。我也想要一个莫扎特成了小朋友们共同的心声。
童年、少年时代几乎都在奔波演出,而故乡始终是他休憩的港湾。直到16岁他才结束漫游生活回到故乡萨尔茨堡暂时安定下来。在保守而封闭的大主教手下供职虽然衣食无忧,但却被侮辱与控制,失去自由的人格。几乎每一部关于莫扎特的传记文学都会提到他最终与大主教决裂的这个桥段,代表着他脱离束缚,成为一位自由音乐家。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由音乐家没有固定收入,意味着生活会时时陷入困窘。既在乐器上还原了莫扎特时代的音色。
在莫扎特的音乐生涯中,他作曲之轻松与神速,和生活的拮据与艰难形成强烈的反差。他音乐里沁人心脾的美妙和欢欣,与凄婉的身世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1791年,在顺利完成《魔笛》的演出后,心力交瘁的莫扎特离死亡仅一步之遥。在创作《安魂曲》的时候离世,由于经济原因没有一场得体的葬礼,甚至连棺木送到墓地的时候,都未有亲友在场。”这是美国音乐学者约瑟夫·马克利斯对他的赞美,一语道破绝代风华。莫扎特拼命工作——教课、演出、创作。
我从萨尔茨堡带回了一盒莫扎特巧克力,这是当地特产,表达了故乡人对这位音乐天才的甜蜜纪念。萨尔茨堡人为纪念莫扎特,创立了莫扎特音乐节,也就是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前身。在赴奥地利之前,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卡拉扬在萨尔茨堡》,这部片子真实再现了晚年卡拉扬在音乐节期间排练、演出、编辑母带等珍贵情景。这位追求完美和艺术极致的指挥家,在排练现场是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纪录片一开始就是跟拍卡拉扬排练歌剧《摩西和艾伦》的过程。它们见证了贝多芬从稚嫩地追随海顿与莫扎特前辈的道路上。
两位主演在他的耳提面命、细节纠错中一定是受益匪浅的。看纪录片时已经明显感觉到两位演员在受到卡拉扬点拨后,歌唱和表演的提升。“由指挥完全掌控乐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我可以做的就是把乐队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让他们自由发挥。你不用紧张,给他们自由,一旦他们意识到该去做什么就会去做。”画面一转,就呈现出他那如大理石雕塑般冷峻高傲的侧脸。在音乐面前他却从来没有任何的专制和倨傲,反倒收放自如而从容。据说有一天,卡拉扬在故乡的悬崖边看到几只雄鹰在天际飞过,顿时感慨道: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遵循了莫扎特的古典协奏曲的结构。
我敢肯定,它们不仅仅为了寻找食物,一定是享受到了飞翔的乐趣。”这位有些高傲追求华美的殿堂级大师,墓地却是在萨尔茨堡附近的一座人烟稀少、清冷寂寥的小镇上。曾经叱咤乐坛,挥棒指点江山,终是洗尽铅华,任由熠熠闪光的丝绒大幕徐徐落下。这里有电影《音乐之声》纪念品商店,还有专门上演《音乐之声》的木偶歌剧院。我们凑巧是在7月底去的,音乐节的预热气氛已经开始在城市各个角落蔓延。街头巷尾常常会看到拿着各种乐器演奏的音乐爱好者,有些乐器古怪得叫不上名字。把莫扎特青年时代研读过的歌剧、宫廷音乐、圣乐所有的乐谱信息和音乐规则输入算法。
走过街道、广场、公园等地,常常看到各种音乐会的海报,也有举着牌子求购某个音乐会入场券的人,看样子端庄文雅得很,似乎不像黄牛党。就在我们去著名的米拉贝尔宫殿和花园参观时,赶上了一场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这座建筑曾是电影《音乐之声》中女主角带着孩子们欢唱"--"的地方。来听音乐会的有穿着奥地利蓬蓬袖衬衫、绣花围裙等传统服饰的女子,也有鼻子、耳朵、嘴角到处串满亮闪闪圈环的嘻哈青年;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莫扎特的思想和风格。
有相互挽着胳膊的优雅老年夫妇,也有蹦蹦跳跳的孩童。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