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看中国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历朝历代的佛造像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以至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无不给予中国的佛像以重要的位置,早期中国佛像流失甚广,今日已是私人收藏和拍卖场上的重戏。而佛像的收藏,首先是要清楚地了解古代中国各个时期佛像的艺术风格以及地区的分类,如:北魏末年到东魏,是青州佛教的大发展时期,这时的佛教艺术品最能反映地区差异,青州佛像的肉髻长细且高,在头顶极为突出,佛像开脸清瘦,带有童稚之气,亲切自然,栩栩如生,而这一风格到东魏时期则更典型,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极其珍贵的精品佳作。

进入盛唐时期,佛教造像呈现了诸多新的现象,长安密教风格开始兴盛,汉白玉成为一时盛行的石材,装饰风格更加华丽繁复,由初唐武周时期所形成的古典主义风格逐渐过渡到以新的现实感与体量感为表现主题的符合中土审美心理的佛教造型。宋代国力渐衰,统治区域仅有现在中国的一半,难有魄力融合各种外来文化,理学成为独尊的时代精神,这在佛教造像中也有所反映。

宋代造像没有北魏那种自信乐观的表情,没有汉唐雄浑刚强的壮美风格,变为温和淡然的清丽气质,显得沉着而朴素,仿佛被一种精神掌控,而在雕塑题材方面,中原信民开始热衷于为观音、罗汉、天王、力士造像,常见木雕彩绘以及摩崖雕凿。菩萨高髻带宝冠,宝冠贴金,呈三叶草式,并饰一串三条悬挂宝珠,冠巾自脑后经两耳后自然飘落两肩,面目沉静,弯眉细目,直鼻樱唇,脸颊及下颌饱满,气质高贵安静;身躯颀长而饱满,颈部配连珠华绳状串饰,下垂一条连珠长链于胸前,袒露上身,下着裙,裙褶顺腿部自然下垂,珠串与飘帛均有一定程度的残损,但仍可见下身飘帛璎珞自然缠绕于体侧,双足裸露站于基座之上。

其整体以白石雕凿,使用多种刀法,将金属、布料、肌肤等多种材质完美表达,服装与肌肤上尚留些许彩绘,更将菩萨富丽堂皇之感表现的尤为出色。造像仅飘带与手部有些许残损,已属极为难得,余下之身躯比例合度,服饰与璎珞等处理清晰明确,给人十分洁净轻盈之感。造像整体绮丽堂皇,又不显繁冗,突显了北齐时期素净、典雅之境界,为这一时代风格之典范。背屏式造像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常见,多成椭圆形、舟形或桃形,在佛与菩萨身后浮雕或阴刻火焰纹、忍冬纹、飞天以及莲瓣作对称及层迭装饰,以图模拟佛教所提倡的经过苦修方能抵达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通常描绘精致,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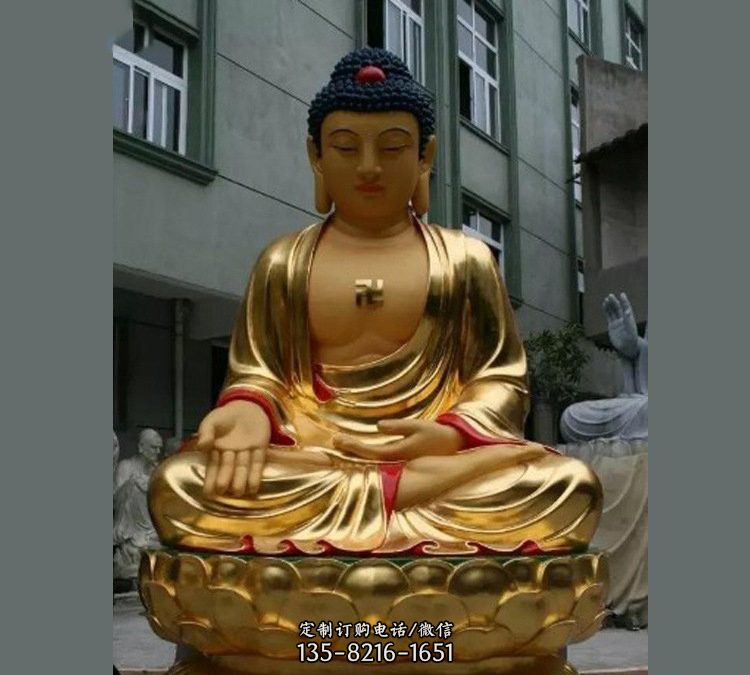
此尊背屏式佛立像即为其中精品,从其遗存部分可见,其完整之时当为一佛二菩萨式样,配至少五身供养飞天,烘托出欢乐和谐的氛围,释尊面露和谐笑容,身体线条流畅,一扫北魏繁重冗余之衣纹,清秀靓丽,整尊背屏像给观者以清新、美好、祥和之感,不失为北齐时期背屏式佛立像之佳作。此尊北齐石雕释迦牟尼背屏式佛立像佛高髻,面带亲切微笑,双目低垂,神态祥和;躯体线条平直流畅,内着僧袛支,外披袈裟,左手予畏印,右手施予愿印,腹部略微突出,袈裟及裙自然下垂,衣纹亦平行向下,起轻微褶皱;
背屏残损,仍可见两身供养飞天,飞天裸上身,戴项圈,下身着长裙,身体弯曲于空中飞舞,灵巧轻盈,生动活泼。从现存实物来看,天王像在隋以前就开始出现,隋代即可见相对清晰的天王形象:头束发配冠,身穿衣裙、护甲,手握拳,脚蹬靴并踩夜叉。唐代,天王像不仅高度人性化,且发展为明确的“四天王”雕塑主题,形成了清晰的标准和规范。此尊天王像面部及衣领处为标准的盛唐风格,符合人体比例,神情与姿态皆自然生动,但面部仍然保留佛国人物之庄严,既改变了隋末唐初天王造像的生硬僵化,亦未沾染晚唐时期过度世俗化的审美取向。
天王半身像发髻上梳,成波浪纹状,面部作愤怒相怒目圆睁,唇鼻立体饱满,轮廓清晰,双唇紧闭,肩覆披臂,身着盔甲,虽残损只留半身,仍可见威武森严之气。此尊菩萨面容沉静内敛,身躯挺拔,气质安静祥和,头戴双层莲瓣宝冠,帔帛自耳后垂于体侧,璎珞于腹前交叉及裙下,左手轻盈下垂手执物,右手抬起手持法器,上身内着僧祗支,下着裙,裙摆褶皱疏简,自然下垂,跣足踩于莲花座上,下身比例略短,头略显大,为隋代典型观音造像风格。隋文帝杨坚立国,即敕令五狱各建佛寺,开窟造像之事风靡一时,山东青州、济南,山西天龙山等地的石窟都极富代表性,这一时期的菩萨常窄肩平胸,婷婷玉立,仪态优美,此尊菩萨像即为个中精品,整体造像华丽规整,洗炼大气,刀法娴熟,品相完整,极为难得。
此尊菩萨身躯饱满,脑后带莲瓣型背光,头戴宝冠,缯带飘落,面带微笑,颈部带珠串项链,璎珞帛带垂于胸前裙下,左手轻盈下垂手提凈瓶,右手持法器,跣足踩于莲花座上,身体比例协调,站立姿势动人,腹微前突,腿部略微弯曲,似行走状,端庄又富动感,为北周典型观音造像风格。此尊菩萨面容祥和,身材颀长,头戴宝冠,后饰桃形背光,背光上装饰单条珠链,璎珞自肩部而下于腹前交叉及裙下,左手轻盈下垂手执凈瓶,右手抬起手持法器,下着裙,裙摆贴体无褶,自然下垂,跣足踩于莲花座上,结构比例协调,为北齐典型观音造像风格。
此尊造像线条流畅,面相清秀,嘴角上翘,略带微笑,刀法精简,通体以连珠璎珞作饰,将观音为众生解救现世苦难之功能与形像真实再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后期民间对观音信仰日甚这一现象。达摩,又称菩提达摩,南北朝来访中国的印度僧人,主张,佛教中国禅宗尊为初代祖师,尊称为、,流传有等传说事迹。禅宗于唐代成为汉传佛教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宣扬甚广。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在宗派上逐渐系统化,因传承而权威,禅宗则是这其中极富神秘色彩的一支。
达摩作为禅宗的初祖,具体何时进入中土尚有待研究,但唐宋时期,随着禅宗的发展壮大,达摩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的面目已经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被神化的佛教禅宗始祖的形象,由此亦可见,唐宋时期是达摩形象在中国得以丰满和神话的关键时期。随着禅宗的确立和发展,记载禅宗的文献日益增加,达摩作为这一宗派的始祖,自然无论在文献典籍之中,亦或宗教美术之中都变得日益丰富起来,成为了一个极富时代风貌的雕塑题材。此尊唐代石雕达摩头像头戴僧帽,额际高广,浓眉微蹙,深目圆睁,乱髯卷髭,作冥想参悟状,刻划极为精美,栩栩如生。
造像表情肃穆,眉宇间神情生动,通过细致的雕刻将达摩亦人亦神之形象尽展无疑,为唐代禅宗造像中之精品。此尊北魏石雕释迦牟尼佛首相面相清秀俊雅,佛高发髻,饰水涡形螺纹,细眉大眼,高鼻小口,嘴角含笑,表情生动,开朗清秀,为典型北魏时期青州石佛之造像。此尊唐代石雕释迦牟尼佛首像面容慈祥睿智,肉髻轻微隆起,表面饰螺纹,眉目修长圆润,双目微睁,眼角稍微上扬,唇鼻轮廓明显而饱满,嘴角略带笑意,整体气质宁静祥和。
此尊唐代石雕释迦牟尼佛首像面容饱满庄严,波纹状发饰、肉髻自然耸立、长目低垂、面容沉静典雅,带有鲜明的初唐风格,面部符合人体的自然构成,柔和而真实,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但仍可见北周、隋代残存的严肃感与硬朗表情,造型技法上注重线、块、面相结合的雕刻性,应为唐代初期两京地区佛教造像的代表作品。此尊北齐石雕释迦牟尼佛首相面相清秀俊雅,佛束发髻,饰螺纹,细眉大眼,高鼻小口,嘴角含笑,为典型北齐时期青州石佛之造像。
北齐,是青州佛教大放异彩之时期,这时的佛教雕塑基本上为单体圆雕,并形成一种标准样式,佛头多为面圆,头顶略尖,额较圆,鼻梁从额中直下并略带弧形,双眼微睁,小嘴略含笑意,下颌突出,双耳下垂,五官较为集中,其形象与新疆克孜尔石窟中壁画形象十分相近,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极其珍贵的精品佳作。菩萨头戴高冠,上饰宝石珠链,宝冠边缘饰连珠纹,缯带自耳后自然飘落,雕饰华丽。面相丰腴,方中带圆,弯眉直鼻,双目微睁,面向恬静安详,形象优美,代表了北齐菩萨像雕凿精致之时代风貌,为河北、山东交界地区之石雕精品。
此石雕罗汉头像应为释迦弟子阿难或迦叶之一,面颊丰腴,表情祥和,慈目半睁,嘴唇微抿,智慧稳重,将释迦弟子之诚诚之心展露无遗。阿难代表多闻智慧,迦叶代表苦行常修,为六世纪末之七世纪初宗教雕塑中之常见题材。此尊唐代石雕释迦牟尼佛首像面容慈祥睿智,肉髻轻微隆起,表面饰螺纹,眉目修长圆润,双目微睁,嘴角略带笑意,整体气质宁静祥和,温润感人。
进入盛唐时期,佛教造像呈现了诸多新的现象,长安密教造型开始兴盛,汉白玉成为一时盛行的石材,装饰风格更加华丽繁复,开始注重对题材的现实感与体量感的表达。此佛首即为盛唐时期佛教造型之代表,其高度汉化的面相代表着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的最高愿景,至此时期,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已被中国社会接纳并吸收,形成了符合中原审美心理的造像语言,对后世佛教美术发展影响深远。罗汉信仰最早源于印度,但在印度尚未见到系统的罗汉造像,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佛教艺术的创造,是佛教美术本土化的重要产物之一。
唐代高僧玄奘大师翻译《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注记》,最早提到十六罗汉。此罗汉首像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罗汉脸部五官立体感十足,饱满的双颊与弯曲的眉目,与同时期佛造像木雕极为神似,整体气质率真爽利,形神合一。绝大部分佛及菩萨的造型多以沉思、肃穆参悟中的状态为基准形象,在重视佛教信仰的六朝时期,工匠在准备雕刻一件佛像时,皆带着虔诚的心态,毕恭毕敬的做好每一步工序,并让精神状态达到一种宁静的境地。
也正是基于此,方能与佛相容,刻画出佛的觉悟式,形成最佳的美感。面部丰腴,面目修长,向两侧上挑,眼睑微开,作俯视状,鼻挺唇厚,嘴角微带笑意,下颚圆满,双耳垂肩,呈雍容闲静之感。此石雕双菩萨从整个雕造工艺和风格特征应为北齐时代,其与山东青州地区所出的石佛像体系相近。两像皆面部肉感饱满,眼部细长,嘴部上翘,微笑慈祥。整个面部的雕刻精致而圆润,身着衣服颇有北魏民族特点,这与东魏北齐风格具有相同脉络。两菩萨双足并拢站立在莲花座上,背后龙华树枝叶繁茂。
虽已是残件,但残缺之美是历史沧桑的赋予,仍可感到造像沉静的神态和高雅的气质。弥勒菩萨,梵名意译为慈氏,为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在大乘佛教中又称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或阿逸多菩萨;祂被视为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将在未来娑婆世界降生成佛。代表其思想之著作为《瑜伽师地论》,相传为无着从弥勒处习得并传述后世,深受道安和玄奘等大师推崇。佛教艺术在北魏就已十分繁盛,兴寺庙,并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到了北周(公元557~581年),佛像造型亦与当时人文背景相称,脸型略方,额头及双颊饱满,身形较丰盈,在六朝中独树一格。
此件石灰岩制菩萨为带冠造型,头冠两侧有饰带垂肩,脸方、饱额、颊丰,眼半闭,嘴角扬,面相喜悦、平和。左手高抬,手心中捧一朵丰美宝花,右手低放,手中亦有宝花在握。唐代曾建都两处,北为长安,南为洛阳,相隔不远,分别位于今陜西与河南,两城比邻而立。唐朝国教为道教,但中原道教与早期佛教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道家理论之影响。盛唐时期石窟作品极为兴盛,精彩首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
据石碑记载,奉先洞始于唐代武周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的特点,面颊圆润丰厚,两耳大,容貌端严安祥,雍容华贵,气宇轩昂,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这点从唐代绘画中及陶俑即可一窥端倪。此件唐代晚期白石刻菩萨立像,身着天衣,胸挂珠链,双手环抱于腹前,双足并,身形丰盈,立姿优雅。由侧面看,可见胸腹曲线,肩形宽厚,双层衣䙓自然垂落于小腹和膝盖前,深具时代典型之美。
婉约、雅容、大度白衣立姿菩萨像,展现出唐至五代时期石雕艺术之美。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成为唐朝开国君主,建都长安。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一度迁都洛阳,以周代唐,史称武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还都长安。唐朝共经历289年,20位皇帝,在诗歌、科技等领域中开创伟业,声名远播海外,并与南亚、西亚及欧洲均有往来。当时长安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丝路也达到鼎盛时期,有许多人慕名前来朝拜,外来使节亦空前的多。
虽然唐代以道教为国教,尊崇《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但因中国与印度来往密切,也有佛学高僧西去取经,多部佛经被译为中文。从留存的名刹古迹、石窟来判断,唐代佛教很兴盛并在民间及宫廷受到重视。常见的力士造型通常头骨较大,脖颈粗,双目凸出有神,宽鼻厚唇,呲牙咧嘴,身披天帛,上身袒露,下着羊肠裙。一般都是成对,龙门石窟的主墙外即可见到这样的作品。
此件白石力士右手弓着提起衣摆,筋骨肌肉线条明显,胸肌厚实,腹肌成排,力量无穷,不容侵犯。虽头首、右臂、双足佚失,但身躯依然气势威猛,有力拔山河之姿,为唐代力士风格之最佳参照。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制造佛像曾被视为亵渎佛陀,当时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笃信佛教,以佛塔、菩提树或是说法座来代表佛陀,而非具体法相。佛教造像的兴盛则起因于当时古印度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伽王一世推崇大乘佛教,并受到希腊艺术影响,雕刻不再以象征符号代替佛陀,而改以写实方式来刻绘人神合一的雕像,因而孕育了二大佛教艺术中心,一是位于西北部的犍陀罗另一则是位于中部恒河上游地区的秣菟罗。
印度佛教艺术于公元1世纪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取经遂透过丝路传入中国及中亚地区,早期佛像为西域风格,自东晋之后,中国风格的佛像才逐渐发展出来,到了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也反映在佛像艺上。北魏时期的石雕造像独具庄严清秀的气质,这种艺术风格在北齐时更为精致而成熟,为中国石刻的一个高峰,河北、山西及山东地区寺庙遗址皆可发现工艺水平极高的作品。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尊隋代的巨型白石阿弥陀佛像,高近六米,亦承袭了北齐佛像的优美样式,是一件可作参考的重要藏品。
学术界经常提及北朝山东青州地区造像工艺之精湛,并称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造像都不如山东的石灰岩造像,但此件白石制北齐佛造像应可改观此论。此外就刻工而言,青州石灰岩属较易刻制的石材,白大理石则更具挑战性。开脸端正庄严,慈悯喜悦,眉型立体,眼垂,鼻直挺,神态威仪。发髻卷结堆积,耳有残损,头与身断后重修,衣饰流畅有型,左肩上有绳结为系,手掌佚失,原应施与愿印与无畏印。工艺严谨,风格洗练,应是北齐时代高级工艺之代表作品。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