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萨里记载的这一幕发生在1520年4月6日的罗马。这一天,年仅37岁的拉斐尔·桑西在重病数日后永别人世。人们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的遗体被安置在其住宅大厅中的美丽灵台之上,四周银烛高照。从清晨到夜晚,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赶来向他的遗体做最后告别。学者们纷纷写下诗篇哀悼,罗马教廷也悲恸不已,教皇亲自为拉斐尔举办隆重葬礼。或许我们可以从6月2日于罗马奎里纳勒博物馆再次开放的“拉斐尔,1520-1483”特展中探寻答案。他在绘画与建筑上的才华令伟大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利奥十世黯然失色…与友人一道游山玩水、酬唱吟诗、叉鱼骑马。

”拉斐尔离世后,教皇利奥十世遵循其遗愿将他的遗体葬入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的公墓——万神殿。在拉斐尔的棺墓上方,他的学生、雕塑家洛伦泽托安置了一尊圣母的塑像。塑像两旁的圆柱上刻下了红衣主教皮埃特罗·本博亲自为拉斐尔撰写的这段墓志铭。墓志铭中提及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是拉斐尔一生中重要的两位赞助人。15世纪末,意大利的艺术中心逐渐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在这里,艺术被看做是加强教会统治的有效宣传工具,而罗马教皇扮演着权利与文化中心人物的角色。1508年初,在同乡好友、同时也是罗马杰出建筑师——布拉曼特的举荐下,拉斐尔前往罗马与佩鲁吉诺、卢卡·西尼奥雷利等老一辈艺术家进行竞争,赢得了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装饰天主教中枢梵蒂冈宫的机会。石刻中的六骏是李世民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

也就是在这里的签字厅顶部,拉斐尔表现了与神学、法学、诗学和哲学相对应的四幅壁画——《辩论》《公正》《帕纳索斯山》和《雅典学院》,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分类和理解。其中,《雅典学院》与《辩论》被绘制在相对的墙上,对应着精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最高权威。不仅渴望成为宗教界的精神领袖,同时希望能成为世俗的领导者。观众可从第八展厅展出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肖像》一睹这位教皇的风采。不同于以往艺术史上教皇肖像的表现方式——人物多为正对观众或侧跪的姿势,拉斐尔笔下的尤里乌斯二世坐在椅上并陷入沉思,椅背上的两个橡实形的装饰暗示了教皇的家族身份:司马迁也保留了作为一个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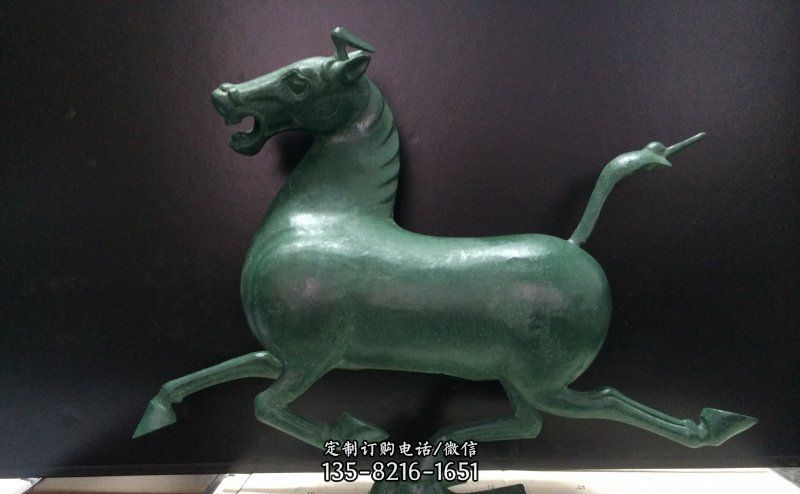
1513年,70岁的尤利乌斯二世与世长辞,新一任教皇利奥十世上任。其中包括在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十幅挂毯彩色底稿,这些底稿后由在佛兰德斯的画家彼得·范·艾尔斯特编织成实物。现存的七幅挂毯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展览选择的两幅挂毯为原尺寸的3D打印制品。挂毯的表现内容均选自《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中圣彼得与圣保罗的生平故事,强调教皇合法地位的权威:是马赛克工艺和新的加工工艺和技术相结合的而衍生出的新的石材产品。

基督教史中,圣彼得和圣保罗是为早期基督教贡献最大的两位圣徒,而圣彼得也是该教历史上的第一位主教,因此他被视为所有教皇的典范。吸引拉斐尔前往罗马的,不仅是热衷艺术赞助的教廷,更是曾经在这里熠熠生辉的古代艺术。从踏上罗马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拉斐尔从未停止过对古代艺术的探索。曾经辉煌若干世纪的罗马古城,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和宏伟的建筑,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建筑倒塌了,又有多少无知之辈把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和其他精美艺术品烧成了石灰!”拉斐尔倍感痛惜,第二展厅展出的文献“给利奥十世的信”,详细记录了拉斐尔对这些破坏提出的激烈控诉,以及他对遗迹勘测做出的讨论,其中还提出了对遗迹进行分类、制图、编目等实操性极强的保护措施。皮影戏相继传入了波斯、阿拉伯、土耳其、暹罗、缅甸、马来群岛、日本以及英、法、德、意、俄等亚欧各国。

这份文献流传有三个版本,此次展出的版本1910年发现于意大利曼托瓦的卡斯蒂利奥内宫,撰写者为拉斐尔的朋友——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一些说法认为,利奥十世收到该信后下令特任拉斐尔为梵蒂冈文物保护专员,但并未有文献能够核实此事。“不过能够确定的是,利奥十世曾委托拉斐尔设计一份关于罗马古代遗迹的地图,而这一想法萌芽于当时上流文化圈研究罗马古物的狂热风潮”。拉斐尔的绘画艺术之名声名鼎赫,但鲜少有人了解作为建筑师的拉斐尔。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如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曾担任过军事工程师。犹如这款手扬马鞭的人物骑马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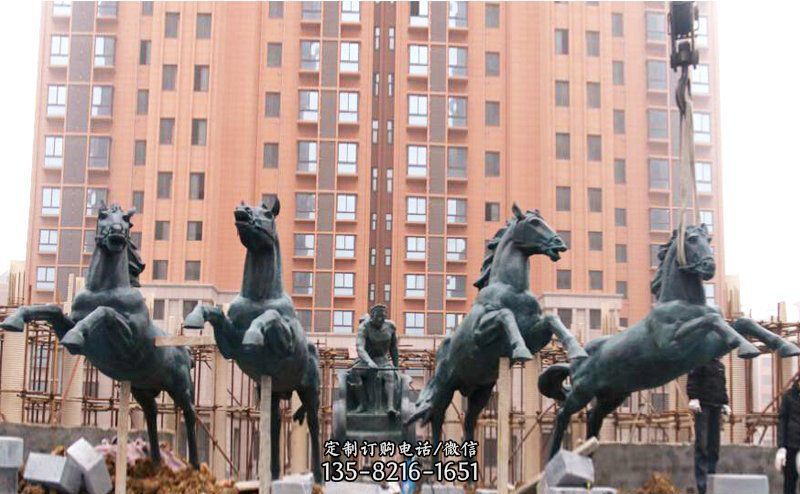
瓦萨里曾对拉斐尔设计的布兰科尼奥·戴尔·阿奎拉宫样图赞不绝口,并且在其《艺苑名人传》中将“乌尔比诺画家和建筑师拉斐尔·桑西”作为拉斐尔传记的标题。遗憾的是,传为拉斐尔设计的许多建筑并未得有实物留存,这也是他建筑师之名未显的关键点。而展览正以“建筑师拉斐尔”为版块,通过展出拉斐尔和其有关的设计图纸、模型等,向观众呈现了拉斐尔在建筑领域所作的探索以及风格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在拉斐尔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建筑的兴趣:马车早叫女粉丝围得水泄不通。

《雅典学院》中覆盖着巨大拱顶的宽阔大厅,《圣母的婚礼》中对背景洗礼堂空间比例的精确处理,等等。而《雅典学院》也许受到了米兰的圣沙弟乐圣母教堂的影响,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再现了于1560年破土动工的新圣彼得大教堂的大致面貌。拉斐尔一直都在刻苦钻研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论著,并从对古典遗迹的实地考察中汲取养分。身在罗马时,拉斐尔以建筑师的身份参与了许多工程,如改造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做的设计,但可惜的是,这些建筑模型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们仍可以从第八展厅的基吉小堂设计图稿中领略艺术家在建筑方面的造诣。1512年,拉斐尔收到为罗马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基吉设计基吉小堂的委托订单,耗时五年,拉斐尔与其学生共同完成了壁画装饰以及穹顶设计等工作。汉字、假名、罗马字对照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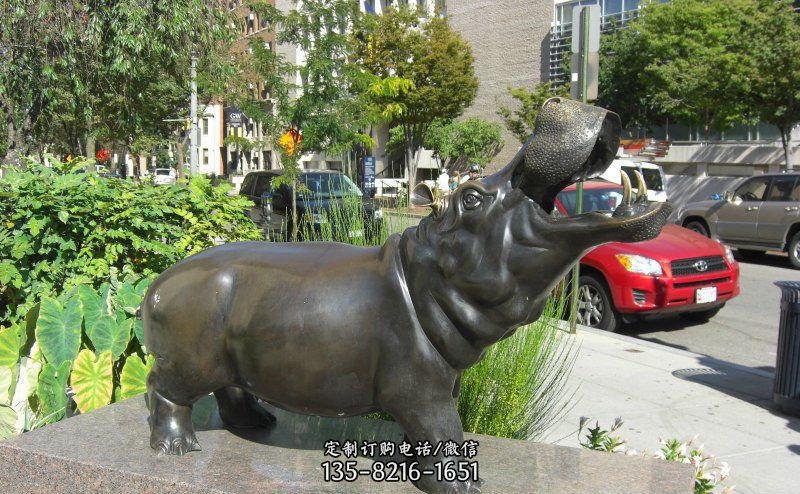
不加装饰的砖块构成圆筒式整体、圆锥式的穹顶,最终汇集到顶部的鼓状式圆筒。布拉曼特曾担任老圣彼得大教堂的改造工程,尽管这项工程在他去世前并未完成,但通过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根据布拉曼特的设计而做的“圣彼得大教堂改造纪念徽章”,我们可一睹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古典、和谐的中心式教堂。而在同展厅展出的拉斐尔建筑设计图纸——罗马布兰科尼奥·戴尔·阿奎拉宫中,拉斐尔在建筑正面增添了窗饰雕刻,以一种复杂、律动感更强的风格取代了布拉曼特式的设计。诸子百家、左丘明、李斯、司马迁、班固、贾谊、晁错。

在基吉小堂之前,阿戈斯蒂诺·基吉就与拉斐尔合作过,并发生一段有趣的故事。“当密友阿戈斯蒂诺·基吉请他为私邸的第一敞廊作画时,拉斐尔却因迷恋一位情妇而忽略了这份工作…但有文献指出拉斐尔在一封写给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的信中否认了这一说法。无论画中女子是谁,优美的形体、深情的目光,对细节的精彩刻画可见拉斐尔对美丽女性形象的炽热情感。他的谋略和智慧为刘邦的胜利和统一中国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展厅前言,拉斐尔笔下的女性是一种希腊-罗马的理想美。而这种美的极致则体现在拉斐尔笔下的圣母题材,《圣母子》中年轻的圣母怀抱着小基督,母子的脸颊互相亲触着,整个画面洋溢着浓浓的母性温柔。画中的圣母形象像是生活优渥、安定的富家女,更具备世俗之美,拉斐尔刻画了圣母所能被赋予的一切美貌。正如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在埃特鲁斯坎文明鼎盛时期还只是村民的罗马人。
“拉斐尔的圣母像是世俗的理想战胜基督教修道院理想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之一。展览正是以“年轻的拉斐尔”作为结束,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艺术家留下了这幅迷人的《自画像》。拉斐尔一生画过许多自画像,而这幅画中的他才不过23岁,但画面中柔和的光线、安定祥和的气氛,体现出这位年轻艺术家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许多学者认为这幅画创作于佛罗伦萨,画面光线的处理方式受到达·芬奇的影响。这里以金甲郝昭、尚方斩马刀刘邦为例。
的确,在1508年前往罗马之前,佛罗伦萨是拉斐尔游学多年的地方。“对艺术的钟爱促使他去了佛罗伦萨,因为锡耶纳许多画家对达·芬奇绘制的一幅非常精美的骑兵画草图赞不绝口,这幅草图将被绘在长老会宫的大厅中,同时,米开朗基罗也画了一些更出色的人体画与莱奥纳多竞争。”这一事件发生在1503年底,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曾在韦基奥宫进行壁画装饰工作。如瓦萨里所述,次年,21岁的拉斐尔便来到佛罗伦萨瞻仰学习前辈们的杰作。着力打造马路公园的景致。
在莱奥纳多的影响下,拉斐尔开始调整以往学到的传统肖像风格。展厅的另一幅作品——《怀抱独角兽的少女》(a,1505)此前一直被认为出自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之手,直到1928年才被艺术史家归于拉斐尔在佛罗伦萨时期的创作。但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背景处理方式出现了——背景的风景不再由程式化的树木构成,佩鲁吉诺风景中的明晰性被一种朦胧的远景所代替——而这正是莱奥纳多常用的方式。拴马桩雕的狮子塑造得粗犷、简练、概括。
不过,拉斐尔的画面并不像莱奥纳多那么浓重和神秘,他仍然偏爱着佩鲁吉诺的明亮调子和清晰的画面效果。五百年后,当人们来到这座城市,仍然可感受到拉斐尔经久不衰的光芒。无论是后世的学院派或是18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都将拉斐尔的艺术奉为一种美的典范。正如文章开头引用的红衣主教皮埃特罗·本博为拉斐尔所作的墓志铭:“这便是拉斐尔,在他生前,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而一旦他撒手人寰,大自然又恐他死去。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