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东尼·葛姆雷是英国知名雕塑家,马丁·盖福德是英国艺术史学者,二人关于雕塑的谈话始于2002年,陆续进行了18年。谈话录体《雕塑的故事》近日出版,他们从“雕塑是什么”出发,回顾了史前至今的造型艺术发展史。不过,谈话不依据年代顺序,而是将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事物放在一起讨论,更为有趣。走进黑暗中,四周一片寂静,所有的干扰都消失了——身处洞穴和早期人造建筑之中时,你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看到了村里悠闲散步的恐龙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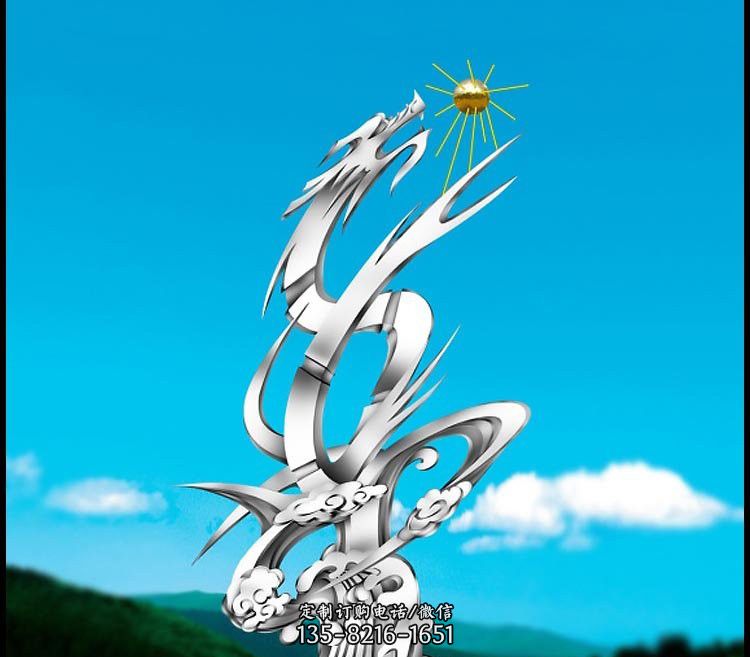
你将尘世的喧嚣抛之脑后——鸟语、阳光、温热都一概抛却——进入一个阒然无声的境地。位于爱尔兰凯里郡海岸边的加拉鲁斯礼拜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旦迈进去,整个船形空间一片昏暗,只有另一头的那扇窗户透进些许亮光,此外再无光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通常都不会把建筑物的内部空间看作雕塑。我们想要的雕塑是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雕刻或塑造而成的形体,而不是一个洞——或可称之为虚空。叶问传授李小龙黐手铜像在孝德湖公园入口附近。

不过有些规模宏大又幽深的建筑结构确确实实是雕凿出来的,比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巴雅、卡利、象岛、埃洛拉和阿旃陀等地保存的早期佛教和印度教石窟。要形容身处石窟内部的感受,用“空无一物”这个词不免有点苍白无力。印度艺术研究专家本杰明·罗兰曾说,走进卡利的大支提窟,洞窟内的一切,包括石柱和舍利塔,似乎都融进昏暗的光线中,神秘莫测。洞窟内部看起来像是木头雕刻而成,实际上却是在坚硬的玄武岩上开凿出来的。北京故宫的桥栏板上雕刻有石雕双龙戏珠。

石窟是在崖壁上凿刻而成的,但建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这座亦真亦幻的厅堂,不如说是为了其内部的空无。谈到这里,我们又到了一个界限不明的地方——我们已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这座建筑的意义究竟是建筑结构本身,还是其内部所包含的东西——虚无?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中,空无并不意味着否定,不是简单的不存在,而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境界,可以让人加深觉悟。我总是搞不清楚什么是艺术经验,什么又是实际存在的。比方说,当你从日常生活的世界走进一个神圣的场所——一个世外之地——获得的是一种存在感还是艺术感呢?在舞龙等民俗表演、在梅山太极拳进校园进社区等全民健身活动中找到自己的生机。

这与表现某种事物无关,而是关乎一种置身临界状态的感觉,很可能真的身处危险之中。仿佛置身悬崖顶端、山峦之巅或是洞穴入口,类似的比喻都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广阔无垠的体验。孤身一人,只能自行其是,这种感觉难以言喻,无法定义。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座佛学院学习,那里有一座专为冥想而设的静修之所。你基本上被封锁在了一个斗室之中,只有一个墙洞供粪便和食物出入。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刻有云龙戏珠和松鹤延年的图案。

这种房间长约1.8米,宽约1.2米,高约2.1米,足够跪拜祝祷之用。进了这个房间,你基本上就能把整个世界抛诸脑后,从而发现自己的精神宿命。走进卡利大支提窟这样一个空间,本应是一种宗教行为。而事实上,空无一物的空间也可以是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关键元素。他的创作参照广泛,包括马歇尔·杜尚、巴尼特·纽曼的作品,以及中国的山水画,此外还有印度的洞窟寺庙。不过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表现石头的重量、体积等性质,相反,他要做的是抵消这些特性——让石头的物质形态消失不见。而犼头下面的部分就是龙柱。

他不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寻觅困在石块中的形体,而是在看似坚实的材料中发现虚无——一道深不可测、黑如墨染的深渊。我一次见到他的这类作品时,真是觉得摄人心魄、十分激进——他在有限之中发现了无限。卡普尔的作品《亚当》是一块高2米多的砂岩,约在人胸口的高度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洞。这就形成一种悖论——眼前虽是一件有限的物体,其中却包含了黑洞中心一般的黑暗,没有光线可以在此存留。有一次我走在泰特现代美术馆里,发现不知哪个顽皮鬼往这件雕塑里扔了一枚小硬币,洞的底部微弱地闪着光,这么一来完全摧毁了无限虚无的假象。像是具有招财作用的动物有石狮子、石雕龙、佛像等等这些。

但是在岩石开凿出的庙宇中,一部分视觉效果恰恰取决于光线渗透进来,捕捉到了室内的雕塑。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小城马马拉普拉姆,靠近海边有一座低矮的山丘,满是露出地面的岩层。在8世纪和9世纪,山丘上的许多岩层陆续被开凿成窟。在石窟内,每面墙上都有雕刻,被从入口射进来的强光照得亮堂堂的。在筏罗诃洞窟内,一幅浮雕从阴影中浮现出来,表现了化身为猪的毗湿奴将大地女神从宇宙之洋中拯救出来的情景。从筏罗诃洞窟步行几分钟,就是马黑萨苏兰征服者石窟。本文修罗将带领大家参观清迈最著名的寺庙:契迪龙寺。

我还记得站在那里观看墙上的浮雕,毗湿奴在原始海洋上安眠,躺在巨蛇舍沙身上,舍沙的头支撑着大地。开凿在山上的石窟在印度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整个亚洲也比比皆是。石窟开凿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河水在石灰岩壁之间奔腾而过。龙门石窟是关于正空间和负空间之运用、尺寸和规模之区别的实例,不断让你根据周围的体量感知自己的分量。就像你之前说过的,对于米开朗琪罗而言,石块仿佛不是“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像斯里兰卡的波隆纳鲁瓦大佛,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直接发生在大千世界之中。古城内的契迪龙寺、帕辛寺、清曼寺和素帖山上的双龙寺。

在洛阳,人们直接从这个世界着手创作——一处基址,一座山峰——无意从山上取下石块,而是让山留在本来的位置,然后将形而上的思考和想象力投射到山崖上。为了做到这一点,秉持着空无之中必有存在的理念,首先要造出一个空间来。这里的十万余尊佛像,都是在随处可见的岩石上原地雕刻出来的。其中许多佛像是真人大小,也有巨大的卢舍那佛,以及成千上万尊比手掌还小的佛像。这就是中外闻名的故宫九龙壁。

在洞窟中,你能亲自观察一点点矿物材料转化成其他事物的形象——具象雕塑的基础——形象就这么在石窟里浮现出来。看起来,这种形式不仅让我们想到大型雕塑的诞生,也让我们思考人类视觉化想象的起源。法国阿列日地区的图多杜贝尔洞窟里,有两只泥土制成的野牛,土直接取自洞窟地面。龙门石窟乃至亚洲其他的石窟寺庙,都是这两只野牛遥远的后代,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同一种理念,即用随处可见的岩石制造物体,又将制成品留在原处,使之成为岩石的一部分。与会大众眼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
其根本在于,回到母亲那里,回到像子宫一样的负雕塑中去——形体由此产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尼奥洞窟,我走了二十分钟才到达所谓的“黑房间”。我想,今天与这里最接近的地方可能是游乐场的魔鬼列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列列的钟乳石,然后是一个个巨大的岩洞,洞顶悬着层层叠叠的石灰岩,因为长期被水流冲刷而变得肉感十足,看上去像皮肤一样,又像是海风吹过、波涛起伏的洋面。这次经历让我想起了梅德尔多·罗索的作品,那种从乱作一团的材料中浮现出形体的感觉。尤其是龙凤比例刻画颇为生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索要表现的主题正是这个——生成的经过,即材料从不稳定的无序状态,转化为可辨识的物体。他将这种先感知然后辨认出某物的体验称为“片刻的惊喜”。当你真正走进这些保存有旧石器时代艺术作品的洞窟中时,你最先意识到的,是岩壁上的种种纹路——起伏、裂纹与瘢痕——如何诱使人类创作出了各种图像:那面岩壁上的突起看着像一个马头,那块石瘤则像野牛的后臀。并在其上分别建雕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爬龙柱和鸟身人面像。
在地下黑暗的洞穴里,这些引人联想的形状,一定刺激了早期人类的想象力。从史前时代一直到21世纪,大量的艺术活动都取决于这种心理机制。我们能在一朵流云中看出人脸或动物的形状,起作用的也是相同的心理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如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和达·芬奇,也都深谙此道。曼特尼亚笔下翻滚起伏、堆积如山的云层,就隐藏了种种形象,包括清晰可辨的人脸、人形,甚至还有一匹马,马背上还有骑手。就连皇帝的龙椅上都是九龙图雕刻。
达·芬奇则建议人们观看旧墙上的斑点,以刺激想象力。你越往这个方向想,越会意识到,空无,即空洞的空间,在任何时期的艺术作品中都是重要的元素,就像在数学中零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数字。芭芭拉·赫普沃斯的《结构》让人联想到洞穴和人体的内部空间,虽然没有真的模仿它们。同时,这件作品还呼应了英格兰康沃尔郡小城圣艾夫斯荒原上的史前巨石。我很赞同,凹陷、孔洞和空地,以及物性和质量的概念,都以种种方式渗透到了现代雕塑之中。天王洪秀全正坐在安庆到芜湖的长江龙船上。
亨利·摩尔和芭芭拉·赫普沃斯所见略同,认为石块上开的洞要比石块本身还有趣,开启了雕塑界对于虚空的关注。这种观念也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建筑与雕塑之间开创了一个巨大的共振场。在赫普沃斯作品《结构》中,内部空间比外在形体更为重要,她是这方面最早的践行者之一。我们知道,康沃尔郡的史前巨石曾是举行重生仪式的圣地。把孔洞视为通往重生的入口,或一个有可能重生的地方,这种观念深植于许多文化中。龙凤在我国的传统吉祥图案中一直以来寓意都是非常祥瑞的。
在撒丁岛的努拉吉文化中,史前人类会在黑暗的地下场所对水进行礼拜,而古希腊人则会到地面的裂缝和洞穴中聆听来自德尔斐和奥林匹斯山的神谕。在康沃尔郡的史前巨石这里,我们有了一种熟悉的联想——柱子与阳物、入口与女阴、圣坛与桌子,跟特尔古日乌的那三件布朗库西作品如出一辙。2009年,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又出现了一个更为现代的“黑洞”。这时候皇宫就有了各种石雕龙凤雕塑。
这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箱体,足有一幢坚实的房屋那么大,作者是波兰艺术家米罗斯瓦夫·巴尔卡。从外面看,这个结构隐隐有种工业感,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比在月黑风高夜的墓地还要黑暗,就是一箱子虚无。你得绕着它转一圈,才能见到一点非常切实的东西,即入口处的一长条亮光。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地心游记》的经历,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对黑暗封闭空间的极度恐惧,而这种恐惧中还掺杂着些许迷恋。虚空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着我们涉足火山口、地下古墓、洞窟乃至下水道?九龙壁是始建于明朝的一种园林建筑。
这些地方召唤着我们,让我们深入黑暗和未知之中,走进有可能被禁锢甚至埋葬的危险之地,同时又引领我们踏上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地下深处的人造结构,重要性不亚于金字塔、塔庙以及方尖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构。印度拉贾斯坦邦的月亮井将我们带入地下深处,井底是一汪反射着天光云影的水面。这简直和室利延陀罗的神秘符号一模一样,重重叠叠的曼荼罗几何图案,将我们引入一个固定不变的中心。斜圆柱的顶端、牌楼的瘠领两端、出檐翘角、横伏两端和立面两处、也都雕以龙头或整条的龙。
20世纪晚期最负盛名的艺术作品之一,基本上就是在地上挖了个大坑,就是美国艺术家迈克尔·黑泽尔在内华达州的荒漠中创作的巨型作品《双重否定》。在内华达荒漠的一个偏远角落,黑泽尔在一座天然峡谷的弯曲处两侧各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壑,两条沟壑加在一起约457米长,这就是《双重否定》。换句话说,这就是地表之上的一个巨大切口,把通常用锤子和凿子做的事放大无数倍之后的样子。这是一个露天的虚空,当然这样的作品也并非黑泽尔首创,远远不是。也叫红毛果、红毛胆、毛龙眼、红胆子。
就像很多乍一看惊世骇俗的作品一样,黑泽尔在自然景观上挖出的大坑固然激进,却也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审视许多年代久远的作品。艺术就是如此,先锋艺术揭示的却是过去,让你从全新的立足点、新鲜的角度来审视已有的东西。黑泽尔的作品很明显和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圣乔治教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也与北美洲西南部的普韦布洛人建造的水井、蓄水池,以及地下礼堂有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建筑的反面,不是建造起来的,而是挖下去的。
埃塞俄比亚的岩石教堂是在一座火山凝灰岩小丘中凿刻出来的,站在坑底朝上看,基本上就是一座朴素的罗马式建筑。但是从上往下俯瞰,效果大不相同——一个凿刻进大地之中的庞然大物,渐渐消失在昏暗的深坑中。黑泽尔的《移走/放回的物体》,是在荒漠或画廊的地面上造出空间,在其中放入大块的花岗岩——石块本身被视为一个物体,重返大地。再一次,艺术中的虚无——一个空间,一道空隙——可以和填充其中的东西同样重要。迈克尔·黑泽尔《移走/放回的物体》,1994年白色花岗岩置入混凝土凹槽中因赫提姆艺术中心收藏布鲁马迪纽米纳斯吉拉斯州,巴西当代艺术家瑞秋·怀特里德就十分热衷于将负转化为正。
通过将热水壶、洗手池之类的寻常物件内外翻转,也就是把容器的内部翻模铸造,怀特里德完成了艺术的一项传统职能,即揭示出寻常事物的结构、美和神秘。雕塑家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创造出和世界上其他事物都足够不同又足够有趣的作品,她就做到了这一点。怀特里德的《幽灵》对于探讨雕塑能做什么、怎么去做的问题,意义深远。这就意味着将虚空转化成一个实体,将房间的内部转化成一个立方体的表面。
它深刻地回应了艺术史上的一系列作品,包括米开朗琪罗所说的和大理石块的关系,以及从替代的角度看,雕塑究竟是什么。她从伦敦一座19世纪的排屋着手,将一楼的起居室变成城市空间的一种重现,而后者如今孕育了绝大部分的人类。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的洞穴,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世界的威胁。这件作品让我们思考自己从何而来,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但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富有质感,正是因为她巨细靡遗地再现了日常事物的纹理——木材的纹路、破碎的地砖。
残留的泥土和盐粒、火炉上的炭灰、护壁条上的积垢、墙面上的种种瑕疵、不合尺寸的镶板门等等,所有这些都讲述着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体验,以及我们在这些空间里的摸爬滚打。如果你想用一件真实存在的物体作为铸造的模具,这件物体必须具有真实性。有很多因素让《幽灵》这件作品真实可信——这是一个位于一层的房间,位于伦敦北部的拱门地区,距离怀特里德出生的地方不远,她家就曾住在这种房子里。《幽灵》难得地体现了个人、概念和形式的精确性,使虚空具有了物质实体。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