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画的人,就算并未经过专业训练,除了画作本身的含义之外,也能轻松感受到一幅画的平衡、比例、和谐。身体各部分之间遵循特定的比例,几乎完美的对称带来平衡。就是这种内在的和谐,使得我们能够本能地感受到画中的和谐。不过,艺术家需要面对完全空白的画布或墙面,需要把它填满:因此,他必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实现平衡、对称、比例。我觉得,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湿壁画的作者,当他想到必须画满如此大一面墙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惊慌。况且,这面墙上的一部分空间,已经安排好用于安置另一幅大画:所以,这幅画周围的部分,也必须足够高大上,不能被那幅引人入胜的作品比下去。拉斐尔与其老师佩鲁基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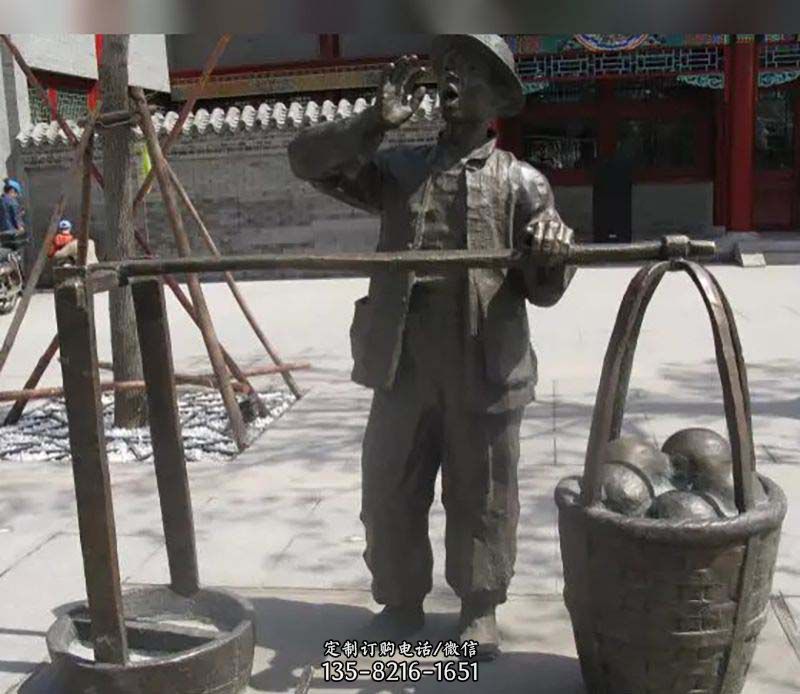
这间修道院的执事,格雷戈里·科尔泰塞,曾经是美第奇家族乔万尼的秘书。这位乔万尼于1513年2月当选教宗,也就是良十世。所以,这位“未来的帕拉西俄斯”必须能够与达芬奇和拉斐尔一较高下,才不会让委托人失望。到底是谁,被格雷戈里·科尔泰塞称为“未来的帕拉西俄斯”?他已经展露出不可限量的能力和探索新事物为己所用的强大意愿。位于圣贝内德托波的波利罗内修道院里,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他叫安托尼奥·阿莱格里,来自科雷乔城,曾经前往曼托瓦,在曼泰尼亚那里学画。这一次拉斐尔将其塑造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斯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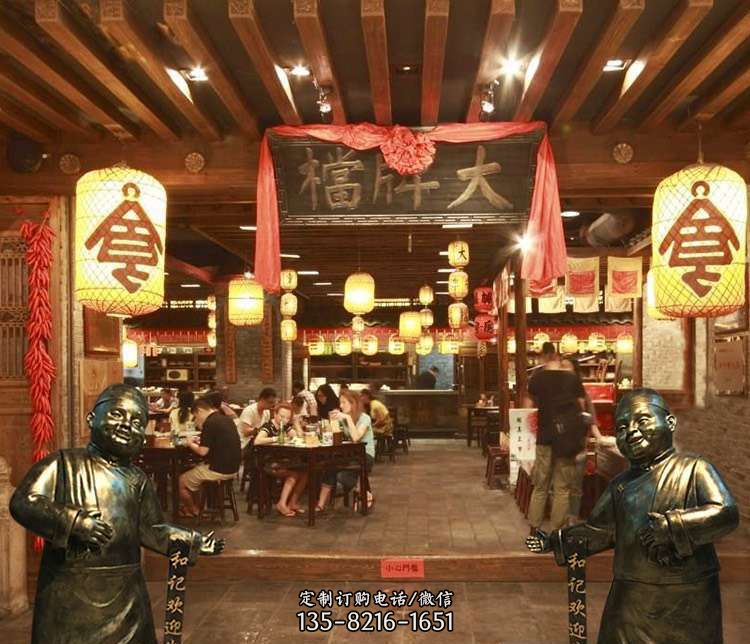
那位大师根本不收没天赋的学生,但却对这个温润的男孩赞赏有加。年轻人学习相当刻苦,在艺术领域极有天赋,特别擅长湿壁画。阿莱格里很受曼泰尼亚喜爱,对于波利罗内修道院的执事来说,也算是一种保障吧。有新教宗的支持,就能走进当时正在修建的圣伯多禄大殿以及梵蒂冈厅堂里,去看看有史以来最伟大作品的施工现场。不过,也有一些特别固执的,认为科雷乔没有去过罗马,因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份书面文件,因此不能证明这件事。对此,我只能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科雷乔的出生证明,但他的确出生了。罗马之行是一场私人旅行,不是为了工作,因此没有必要留下痕迹。沙发拉斐尔纳沃特弗里德曼本达画廊这款柜子融合了日式的极简主义与西方的现代主义。

科雷乔曾经参观过罗马城的杰作,从他旅行之后的那些作品中就能看出来。他还清晰记得拉斐尔《福利尼奥版圣母》中圣若翰洗者的形象,他画中的描绘几乎一模一样。这幅《圣方济各版圣母》中,圣母坐着的那个台座上,有一个椭圆,里面画着梅瑟,恰恰与米开朗基罗不久之前刚刚完工的雕塑姿势一样。此外,在帕尔马圣保禄修道院女院长卧室中,也能发现他画了一些小而有趣的雕塑,全都引用自古罗马雕塑。讲给大家听:拉斐尔画了一个小孩面对一串葡萄垂涎欲滴。

那些熟悉艺术的人看到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湿壁画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与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似乎相似。两幅作品都展示了巨大神庙的内景,里面有许多圆柱或墩柱,支撑起巨大的筒形拱顶,还有一个圆顶,虽然未见却能猜想得出。两幅作品都展示了巨大神庙的内景,里面有许多圆柱或墩柱,支撑起巨大的筒形拱顶和圆顶。福音书中写道,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一间宅子的宽大楼厅里,房间已经铺设好了,准备迎接逾越节。由于拉斐尔是操治愈术的天使。

科雷乔显然征得了院牧的同意,在画中讲述了这件事的起源,描绘了久远往事的场景。还描绘了领圣血圣体的伟大时刻,作为最后的晚餐的遗产。由于最后的晚餐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应该需要一个宏大的背景吧:但是,这里有多个元素与圣经描述吻合,包括家具、灯和烛台,以及室内的金色装饰。里面描绘的人物也是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人物,而不是拉斐尔那样使用雕塑。弥尔顿的原作主要讲的是天使拉斐尔应亚当的请求。

这幅湿壁画虽然在拿破仑攻打意大利期间遭到破坏,但是依然具有相当复杂的构图,能够看出双柱、拱形结构、筒形拱顶和圆顶。因此,建筑师格拉齐娅·斯格里利能够精确重建这幅场景的平面图。从中可以推论得出,左右两侧双圆柱的后面,各开有两个侧面小堂,而中央身廊中,则有两个大圆顶,一个就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另一个则在后门前方的廊柱隔间上方。如此构图,不仅符合严谨的建筑构造,同时室内部分也很有新颖之处,其中许多构造元素,都来自恢弘丰富的古罗马艺术以及基督教早期艺术,与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模式融合在一起。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丁托列托、伦勃朗等众多的各画派代表人物作品而驰名。

在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中,圆柱落在雕有塑像的高台座上;这盏灯很有威尼斯特色,既像珍贵首饰,又像玻璃器皿,由威尼斯奶白色玻璃罐、复活节蛋、中央玻璃珠构成的小十字架。这盏灯代表着天主的真实存在,在它之下,就像置于无形的保护之下。它不仅与“诞生”有关,更与“重生”有关,因为它循环往复,推动一次又一次的复生。因此,我觉得,从天上悬下来的灯,通过这样的构思,完全符合下方基督的形象以及最后的晚餐这一事件。从立体角度观察这幅作品时,必须注意到,规则的透视是通过倾斜的顶层壁带、柱头、柱枕来实现的。当然,这里是中央透视,消失点或视线点位于中线上和基督胸膛处。拉斐尔以建筑师的身份参与了许多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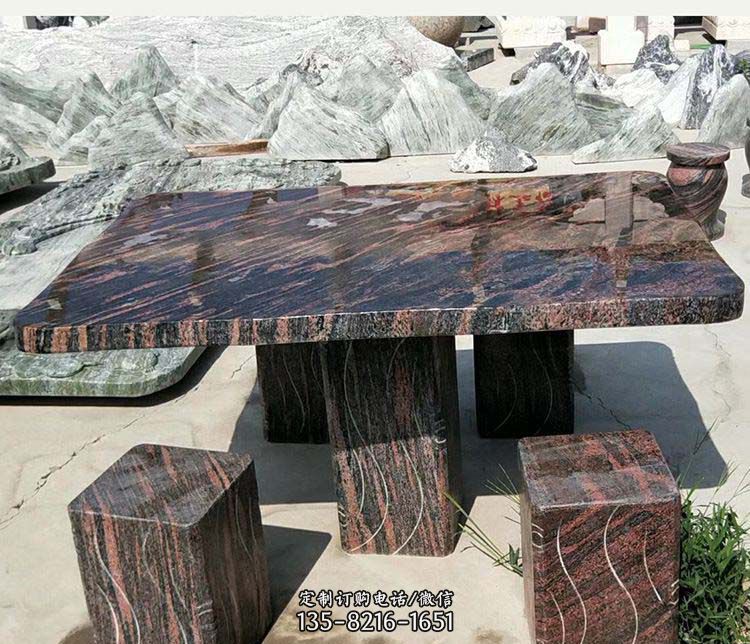
但是,艺术家在平面上作画,也就是说,一个二维表面,因此,需要借助几何方法,来完成全部建筑构造。但是,为了更好地将注意力引向最为重要的事件,需要利用规则的几何图形来创造出一个和谐整体。在这里,与之后其它作品中的做法类似,科雷乔使用了正方形。其边长为长方形画作较短边的长度,也就是画作的高度。两个柱基上,左边画着亚巴郎与依撒格,也就是祭祀主题,右边画着默基瑟德,也就是奉献饼和酒的主题。所以,它是一个标尺,将正方形侧边进行三等分,于是分成了九个小正方形。其中两个小天使的原型是拉斐尔偶然在街道上偶遇的两个玩耍的孩童。

在横向分割方面,可以注意到,上中下三条中最下面一条布满人物,上方的两条则主要是建筑。中间一条有中景上的圆柱,最上面一条则是拱形结构和拱顶。中间一份的两条边线与地面垂直,恰好与画面背景上后门前左右拱形结构的边缘重合,也就是两个侧边小堂的起始点。此外,这两条线还将彭西尼奥里《最后的晚餐》中耶稣两侧的那两组宗徒圈了进来。如今,科雷乔画中的中门是修复时画上的,但也是根据《最后的晚餐》中的门框柱画出来的。在拉斐尔过去创造的圣母中。

科雷乔在之后为帕尔马圣保禄修道院女院长卧室穹顶绘制的湿壁画中,也描绘过坐在门前的基督。现在再来看一下小正方形,以为边长,相当于大正方形的九分之一。使用圆规,固定在B点上,半径长度等于对角线的长度,于是可以找到另一个点H。也就是说,小正方形边长加上台座的宽度,等于小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在中间一横排左右两边的小正方形中,也能找到同样的等腰三角形。从大正方形最上方中点P处连线和,这时又出现一个等腰三角形,与之前的等腰三角形相似,里面有:拉斐尔计划将人物设置在一个简单的石墙前。
背景上带有牛眼天窗的圆顶、背景墙壁和“门”、整幅《最后的晚餐》。此时,基督降临之前的那些人物都在大等腰三角形之外。因此,《最后的晚餐》,作为《新约》的盟约,不仅被安排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而且还要将基督放在中心,因为他本人就是是新的神殿;作为先兆的依撒依亚,出现在基督形象的正上方,被当作背景中央拱形结构的拱心石。我们刚才提到,波利罗内修道院的湿壁画与拉斐尔《雅典学院》构图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后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
当然,这里的神庙根本不是希腊式的,看上去更像是正在修建的圣伯多禄大殿。这一场景的视线点位于中线上,在中间两个哲学家之间。刚才我们对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的湿壁画进行了分析,现在让我们对拉斐尔的作品进行分析。考虑绘画纵向高度方面,可以看到,下半部分完全被人物占据,上半部分由建筑及相应装饰、天空占据。如果我们将湿壁画高度作为边长,构建一个正方形,此时就会意识到,这个正方形可以被分成四部分,可以将左侧真门旁边画上的那个大理石小底座上表面的高度当作小正方形边长。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
小底座出现在大正方形之外,就像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的湿壁画中的柱基。将大正方形分割成十六个相等的部分,可以注意到,最高的那条水平线恰好与中央拱顶上弧线相切;中等高度的那条水平线略略高过哲学家们,但精准擦过左右两边最高个的头顶。中低高度的那条水平线恰好与第欧根尼所躺台阶最上面一阶对齐,同时精准擦过正在方块上书写的那个人的头。这幅画的轴线将两位伟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开,每一位的追随者都在各自的小方块中。由于对学院推崇的以拉斐尔为范本的形式化教育不满。
这幅画的轴线将两位伟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开,每一位的追随者都在各自的小方块中。而科雷乔1518年在帕尔马圣保禄修道院女院长卧室穹顶湿壁画中,似乎全都是神话内容,但背后却有圣经解读方式。现在,我们就能看出,在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这幅画中,科雷乔从拉斐尔那里借鉴了不少。不仅是利用正方形划分任务这一概念,同时也有如何利用标尺划分空间。两人都使用了柱基作为标尺,并且将它留在正方形之外。因为,波利罗内修道院斋堂这幅画与梵蒂冈厅堂中的那幅画太过相像。必须记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内心深处总是想要去看、去了解、去获得新的体验,他无法抑制,想要去走动、去结识其他人、去丰富并滋养内心的火焰。而佩鲁吉诺是拉斐尔的老师。
安托尼奥·阿莱格里懂得如何去看、去理解、去向内投射新鲜事物,然后对其进行加工改造,推陈出新,因此才能在帕尔马主教座堂圆顶湿壁画中攀上绘画生涯的巅峰。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