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株碧桃都从根部断裂,趴在雨中,受它们拖曳,路灯都坠地了。四年来,高邻对它们始终“心太软”,他读哲学的,常说,用木头做雕塑,做车轮做家具都是违反木之本意的,因此对院内花木一律不剪不裁不锯不斫,任其野蛮覆盖,自由生长,美其名曰“全性保真”,顺其自然,充分发展个性,结果却导致半夜里的“呱啦”!碧桃很美,花型似桃而色逾丹朱,但从不修枝的后果一定是疯长,都长得像雨棚了,哲学家还不断地给它们上肥,前不久一位通园艺的朋友来看他,说“慈不栽树”,你把它们宠坏了!灵隐寺的一棵老松树要被砍伐。

好了,现在“生命”给颜色了,除了后窗,他的前院更狼藉,平日里宠得脑满肠肥的几乎全部倒伏。我隔着围墙,举着德国钢锯对他桀桀地笑,他探过头来才明白,我家的桂花、杜鹃、香樟到红叶李,没一棵倒伏的,问为什么,我又举了举钢锯。我其实最初比哲学家还宠它们,宠得杜鹃光拔骨架不开花,天竺大得像芭蕉,紫荆密得像冬青,我却始终怕它们疼而不斧不钺。然它们对我的回报就是两个字,疯长,根本不顾大家的感受,满院子的张牙舞爪,挂灯结彩,老同学来闲聊看不下去,操起斧钺就是一顿暴砍,然后不久月季开花了,石榴挂果了,紫藤婀娜了,紫荆窈窕了,“你这叫慈不掌兵,懂伐?杜少陵饮中八仙歌复有皎如玉树临风前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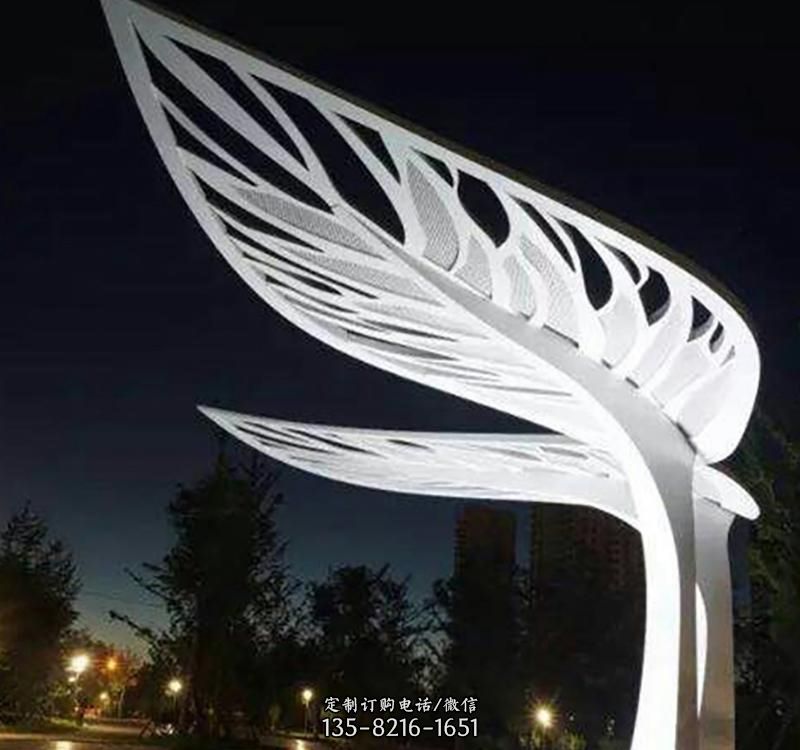
如果容许我们有时间坐下来想一想,大部分的学员可能都会搭下一班的火车离开这里!”——“斯巴达式”的训练与体罚,让你想死的念头都有,但反对无效,以至于校内最著名的一句服从就是:删别人的,手起刀落把头砍掉即可,“鱼烂从头始”,盖常人的文章一般“啰嗦”都在头也,看过菜场里刮鱼鳞吗,哪一刀不是从头开始的,但删自己的文章就忸怩作态了,敝帚自珍,这一行舍弃不得,那一段妙不可言,又一处微言大义,人的自恋就这德性。公园最近出现了树脂工艺品。

其实呢天下哪有不可删的文章,《论语》16000多字,夫子教学四十年,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弟子三千贤人七二,才说了这么些话?可见大量的“圣人之言”早被“辣手”们舍弃了,《论语》尚且能舍能删,还有什么文章不能动的呢,《吕氏春秋》曾自吹一个字都动不得,事实上不正是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吗。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