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醉醺醺地瞪着我们,眯着眼睛,眉毛弯弯,他那鼻子长得离谱,向下垂着,耳垂也低低地耷拉着,上面还打了很大的耳洞。他怪诞、滑稽、又微微怒嗔,是个来自远东的古代小丑。在这里曾经存放了公元6世纪到9世纪之间从亚洲各地收集来的举世珍宝。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珍宝阁,藏有乐器、雕像、珍贵的木雕与绫罗绸缎。因为人们相信,这个面具可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的扑朔迷离的海外粟特人在最遥远的东方的见证者。

现在,我们来到四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在世界的另一端,法国东北部的南锡。这是一块纺织品,织品上浓郁的蓝色与橙黄早已褪去,两头肃穆的狮子盘踞在一棵棕榈树的两侧,周围环绕着一个奖章的纹案;有人说,这块用于包裹一位欧洲圣人遗物的精美织品源自粟特人之手。在世界两端的法国与日本这两个宗教文化的宝库,是否真的都保存着来自粟特这个欧亚大陆伟大、失落文化中尘封已久的碎片呢?自从德国制图师与探险家曼弗雷德·冯·里希霍芬在1877年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以来,我们一直对连接亚洲与欧洲、横贯“东方”与“西方”大陆的贸易路线充满了神往。在某种程度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现代人头脑的产物,人们热衷于为相互关联的、“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寻找根源与谱系。

在阿富汗中部的密室里埋藏的一个埃及玻璃杯,在欧洲大教堂里发现的一块中亚丝绸。我们陶醉于跨越这些大陆的商人与旅者,他们收集与分享着知识,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流转。古人也与我们并没有那么不同,又或者说,我们与他们也没有那么不同,这让我们感到慰藉。这样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能够阐明、甚至证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所持有的价值观:20世纪初发现并破译了大量的粟特文献,这对从事这一探索工作的学者来说是巨大的福音。

因为在粟特人身上,我们似乎发现了丝绸之路上的那些杰出的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尤其是三十年間,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尝试着在世界各地追寻粟特人的踪迹。他们在中亚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这些地区的多个遗址都有着大量的发现与考古发掘,揭示了当时的城市布局;这些粟特文化的具体文物使我们能够勾勒出在丝绸之路中心地带的粟特人民的生活画面。从南锡到奈良、从曼谷到比利时,我们能在整个丝绸之路上都找到粟特人的踪迹吗?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从未在其本土之外发挥过巨大政治力量的文化。在史学术语中,我们会把他们称为“庶民”—社会地位较低的属民,而不是通常主宰历史的那些“伟人”—如君主、将军或圣贤。因此,要想追踪粟特人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我们就必须将分佈在外国编年史中,对他们的零星记录拼凑起来,分析来自欧亚大陆的物质证据,以寻找某件物品可能源于粟特的迹象,并在其他国家的艺术作品中寻找对粟特人的表現。

这样的求索将是不完整的、试探性的、推测性的,但也是令人兴奋的。寻找一个失落的民族也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这是一种拯救历史的方式。首先,让我们从拼凑在中亚与中国以外的与粟特人以及與他们文化有关的文本、物质证据开始,以图了解他们贸易与影响的潜在范围。其次,我们将考虑在外国艺术品中对粟特的表征,以衡量他们的传播范围,即使没有物质留存,至少捕捉他们的形象与声誉。

在分析文本与物证时,我们最好从靠近粟特和中国西部的粟特人故乡开始找起,在哪里有更为可靠的基础,然后慢慢向外发展。从粟特东南方向的印度开始,我们当然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断出粟特人是在他们的家乡与印度之间、以及印度和中国之间活跃的商人与旅者。关于这一点,我们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夏提欧地区发现的刻在岩石上的铭文;这些铭文是在1960和70年代修建喀喇昆仑公路后发现的,公路的修建使得考古学家们得以进入巴基斯坦以前无法到达的地区。这些证据甚至表明,粟特人在粟特、印度与中国这个三角地带拥有“有效的贸易垄断”。

除了这些铭文,我们还有关于深入印度并在那里定居的粟特商人的零星记载。还有在中国文献中关于一位粟特佛教僧侣的记载,这份资料中说他来自一个在印度生活了“许多代”的粟特家族。从印度北部继续向东推进,我们还能一瞥在西藏的粟特商人与工匠的风采。他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麝香,这是一种藏鹿所产生的有特殊香味的物质,因能用于制作香水而备受推崇;从1907年在中国西部发现的古代粟特书信中,我们得知,粟特人从事这种麝香的交易。

他们为此声名远播,以至于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叶耳孤比说“粟特麝香”仅次于“西藏麝香”。叶耳孤比同时还提到“呼罗珊”的商人会前往西藏购买麝香,然后返回家乡,然后从他们的家乡将麝香出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在西藏曾经出现过粟特工匠,在那里,他们的金属加工技术似乎很受重视。如果我们继续穿越南亚和东南亚,现在必须走一条不同的路线:

研究前伊斯兰中亚地区的优秀学者弗朗茨·格雷内为越南和斯里兰卡存在粟特商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在越南,我们有一份公元5世纪的资料,是一部中国佛教僧侣传记集。该文集讲述了公元3世纪的一位名叫康僧会的僧人,他的家人与其他粟特人一起在印度生活了“数代”,后来他的父亲将家安在了“东京”,现在的越南境内。这个姓氏是来自康居地区的家族所使用的的名字,在当时,这个地区主要是指索格底亚那及其周边地区。在斯里兰卡,我们的主要资料是关于一百多年以后,公元5世纪时期。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位中国取经者,法显所写的文本,其中指出在斯里兰卡的阿努拉德普勒可以找到“萨波”商人。虽然萨波并不一定是指粟特人,但我们还有另一份资料支持粟特人生活在斯里兰卡的说法:不空三藏法师的传记,不空三藏法师是公元8世纪中国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法师。这部传记中说,不空三藏法师出生在斯里兰卡,他的父亲与母亲来自康姓家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最有可能指的是粟特,这两个资料放在一起,是佐证粟特人曾在斯里兰卡定居的有力证据。继续向东,我们到达了丝绸之路最遥远的目的地—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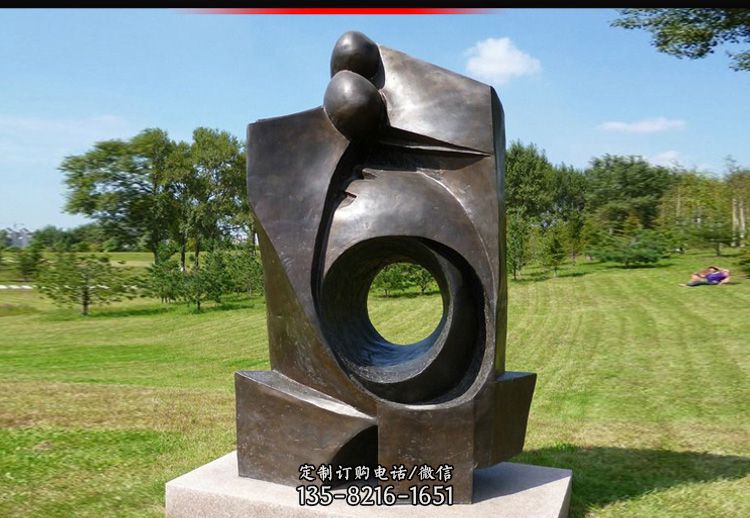
可惜的是,尽管鉴于唐朝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深远交流,粟特人极有可能曾实际前往或者在日本当地居住过,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已知的资料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我们确实在奈良的正宗院和法隆寺的寺庙中发现了关于他们商业遗存的证据。佛教徒非常珍视檀木的香气,禅修者认为檀香可以保持警觉,用印度巴利语写成的佛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两根檀香木上刻有巴列维语,这是一种用萨珊王朝后期的波斯草书书写的语言,上面还刻有一个粟特语印记。这个印记很可能是一个粟特商人的商标,檀木很可能在从印度或斯里兰卡到达日本的途中曾经他之手。
在我们一路向东,搜寻与粟特人有关的文本与物质证据之后,是时候回溯的脚步,从粟特向北,进入欧亚大草原。从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这片广袤的平原,向东延伸到蒙古国与满洲里,向北、向西进入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粟特人是否曾经利用到他们北方这个广阔的经济与文化区呢?我们确实可以在6至9世纪的考古和书面证据中找到粟特过去的踪迹。在那里,粟特人成为了中国人和索格底亚那北部游牧民族之间成功的中间人。随着6世纪中后期突厥人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建立统治,欧亚大陆的贸易步伐加快。
大草原和索格底亚那地区之间交易的一种主要商品是奴隶,我们有书面证据表明撒马尔罕是北部草原和中亚其他地区之间奴隶贸易的中心。向北走,我们从生活在大草原的游牧贵族的墓葬考古发掘中了解到,从中亚进口的镜子、纺织品和金属制品是当时的珍贵物品。然而,我们很难判断这些物品是作为战利品、外交礼物还是通过贸易收集来的。因此,很难区分粟特人在这里扮演的是此类商品的制造商还是贸易商的角色。
沿着草原向东行进,一直到达蒙古,我们还可以一瞥粟特人作为著名的马商和工匠的风采,有些人还曾在那里的突厥法庭工作。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粟特人曾在这里有过经商活动,但我们可以推断出粟特人曾在这里存在,因为鄂尔多斯北部地区在中国和突厥语中都被称为“粟特六州”。蒙古国,后杭爱省,鄂尔浑河一号遗址,公元735年以前。盟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乌兰巴托,2003-4-43.在蒙古国也发现了粟特生产的物品:
在蒙古国的鄂尔浑河一号遗址发现的一个宝藏中有部分鎏金的银质雕塑,近期研究认为这是粟特的制品;考古学家索伦·斯塔克提出了制造这个雕塑的三个可能地点:索格底亚那当地、索格底亚那以东的粟特人殖民地、甚至可能是蒙古中部的东突厥居住地。另一个远离产地的粟特工艺品是在俄罗斯阿尔泰目的发现的一把剑;同样,我们很难知道这把佩剑是在哪里制造的,但是它证明了熟练的粟特工匠在遥远地方的影响;
如果粟特以北遥远的草原见证了粟特商人、工匠和货物的远征,那么我们能从波斯、中东和欧洲的西部旅程中找到什么?这也许会让你感到惊讶,我们在毗邻索格底亚那地区的西边,也就是今伊朗地区,几乎没有发现粟特人的踪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统治该地区的萨珊王朝不想让粟特商人取代萨珊商人进入利润丰厚的西方市场。在公元6世纪的中后叶,粟特人接近萨珊国王,希望能得到其批准在那里出售丝绸。在这个事件里,粟特人并不是试图售卖粟特布匹,而是与他们的突厥盟友合作,试图处理突厥人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盈余丝绸贡品。
粟特人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是建议突厥人尝试着直接与萨珊人的敌人拜占庭人进行贸易。尽管关于这个建议结果并没有详述,这个事件表明了很重要的几点:粟特商人可以扮演外交官与中间人的角色,而且萨珊人对于他们的贸易边界有着保护主义的立场。通过高加索过境的丝绸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在萨珊王朝时期而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都在高加索西北部的莫谢瓦亚·巴勒卡墓葬遗址的主要发现中得到了实物证明。在8世纪上半叶,索格底亚那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穆斯林军队之手。鲍里斯·马沙克认为粟特的工艺传统继续影响着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的银器生产。
他甚至将现存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中的两个银盘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儿子之一马蒙联系起来,他在9世纪的前十年中持有呼罗珊地区的领地。正如艾蒂安·德拉·维西埃所强调的那样,阿拉伯人的征服虽然逐渐推进,但是并没有立即击垮粟特社会。传统的粟特精英们在9世纪初叶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继续进行反叛。粟特贵族阶级的军事巅峰无疑是在马蒙和他的继任者穆塔西姆在任的时期。
在阿拔斯王朝宫廷中,粟特军队中最重要的是乌斯特鲁沙纳统治者的继承人阿夫辛·海达尔,他的宫殿是巴格达北部阿拔斯王朝萨马拉城所有建筑中最大的一座。阿夫辛·海达尔被指控拥有偶像崇拜、镶有珠宝的雕像和带有插图的宗教文本,但尚不清楚这些物品是否属于佛教。首先,他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手稿,况且,法官自己也拥有动物寓言卡利拉瓦迪姆纳的副本。从这里,可以推断出法官的副本是有插图的,我们发现7世纪后期粟特壁画与后来在中东生产的手稿之间的艺术回响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例如,在粟特的片治肯特市,考古学家发现了描绘印度《五卷书》故事的壁画,这是一个最早用梵文写成的动物寓言。
这些图画被分割成了环绕大厅下部的多个小版块,描绘了一群会说话的狼、骑在乌龟背上的猴子、以及被野兔欺骗而跌入水潭中的狮子。这些插画的形式、主题和风格上的呼应也出现在阿尤布和马穆鲁克时期的阿拉伯手稿中。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说粟特人的壁画对随后的阿拉伯手稿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呢?一位学者认为,粟特人可能在他们创作壁画的同时也绘有图画手稿,并且这些文本有可能已经向西传播到了阿拉伯世界。但是,又或许,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早期插画共有的传统在多语言多地点之间来回传播之后,粟特和后来的阿拉伯传统都从中汲取了灵感。20世纪50年代,似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比利时休伊圣母院大教堂的一件纺织品的背面发现了据称是粟特文的记载;
根据粟特语言学专家W.B.的观点,铭文中的关键词是“”,10世纪历史学家纳尔沙希曾用这个词描述在赞达那地区生产的纺织品。“这太幸运了,这个名字的铭文在一件织物上被发现,这在纺织史上独一无二,或许就能认定这件织物来自这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不过,谢波德的兴奋是没有根据的,他掀起了一场长达50年的疯狂追逐,学者们将“”这个标签应用于不断增长的丝绸语料库中。这种认定的第一个问题是认为中世纪对赞达那纺织品的描述是指棉花,而不是丝绸。
原来,休伊纺织品背后的“粟特”文字根本不是粟特语—是阿拉伯语!然而,对休伊纺织品的错误认定并不排除索格底亚那是这些欧洲流通的中亚纺织品的生产地。这些面料显然是在一个可以借鉴西亚技术和设计理念以及中国人对颜色和染料材料的品味的地区生产的。但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和风格研究之前,这些中亚丝绸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有文字和物质证据加在一起,有力地证明了粟特人的实际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受到贸易的诱惑,前往了远离粟特的各个地方。
证据还表明,粟特工匠生产的商品或粟特商人交易的商品遍布欧亚大陆的广泛地区。我们对海外粟特人存在的最后一类证据是在亚洲各地发现的艺术品中对他们的表现。粟特人在外国的存在似乎确实促使当地的艺术家—尤其是在中国—常常用一种接近漫画的奇思妙想来描绘粟特男性形象。中国出图的唐俑中所描绘的许多异国情调的人物如今都被认定为是粟特人,基于他们身上的各种特征,例如鹰钩鼻、浓密的胡须和肥胖的身材;
在中国的粟特形象中,舞蹈与音乐是显著的特征,有些人物演奏的是中世纪琉特琴的前身琵琶,还有一些则是在表演一种被称为“胡旋舞”的舞蹈时疯狂地手舞足蹈;这种舞蹈在中国很受欢迎,尤其是唐玄宗对这种舞蹈甚是喜爱。一是,虽然这些随葬人物显然具有异国情调,但没有一个被明确认定为粟特人。中国的工匠和公众可能会将他们视为一般的“西方”人物,而不是将他们具体视为是粟特人。如果要将他们归类为粟特人,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依靠证据而不是推断。
第二个问题是,在粟特的粟特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例如,在片治肯特的壁画中,粟特宴会的人往往身材高大,肤色或许白得夸张,有着黄蜂腰和精致的五官,通常也不蓄胡子。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大腹便便、粗暴的福斯塔夫式粟特人物形象截然相反。幸运的是,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粟特人在唐以前和唐朝的中国是如何描绘自己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考古学家在西安发现了两个粟特人的浮雕墓葬——史君和安伽,这两位在中国的粟特人社区的杰出领袖,也叫萨保。
让我们把安伽墓榻上描绘的情景中的中心人物与来自片治肯特的一幅壁画上的骑士宴会图上的人物进行对比。画面中的二人都是在享受宴会,但是片治肯特的壁画上人物是纤瘦的,而安伽的身材则是十分圆润。国家冬宫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16235不过,安伽并不是唯一一个肥胖的粟特形象,据报道,在安阳发现了一座无名的石榻;这种明显不同的人物形象很可能是由于阶级和形象的差异。在片治肯特,画面中的人物可能是坐着,但是他们自豪地配着剑,显然是属于骑士阶层,他们在狩猎和战斗中所展现的骑士精神在片治肯特和阿弗拉西亚卜的其他几幅壁画中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粟特萨保是商人社区的领袖,对他们来说,丰满的腰围是世俗成功的标志。
墓榻上的场景里那些盛宴可能是与某种仪式有关,但饮料、食物、音乐和舞蹈显然是这些外籍粟特人生活乐趣的表达。在一个将西方的幻想和时尚带到唐都的社区中,这些反映了粟特人更广泛的文化特征。”没有什么比图21这个来自西藏最重要的寺院里巨大的银质鎏金壶上的三个场景更详尽、更有表现力地描绘了那些沉醉于狂舞、音乐创作与饮酒的胖子、大胡子形象了。
这里是拉萨的大昭寺,由吐蕃王朝的创立者松赞干布建立。在第三个场景里,他身体苏软,昏昏沉沉,耷拉着脑袋,倒在两个无助的同伴怀里;关于这个大壶是否是在西藏由西藏银匠制作,还是由在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所制,学者们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讨论。似乎没有争议的是,画面中的这位音乐家应该是个粟特人。这个大壶的壶嘴采用骆驼头的形状,可能指向这是丝绸之路的产物。
对舞蹈着的音乐家如此生动的描绘和颇具戏剧性的细节使之超越了对一般人物的表达,这很可能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的描绘。这个壶很可能是用来装酒的,其上所描绘的形象生动地从视觉上展示了酒精饮料令人沉醉的效果。联系到松赞干布,这个酒壶反映了他对饮酒的兴趣,足以让他两次在《唐书》上被提及:一次是说他进贡了一只可以盛下十加仑酒的大金鹅,另一次是说他在公元649年请求唐高宗赠送他酿酒所需的工具。
集中体现了粟特人这种放纵嗜好的是唐代的将军安禄山,据埃德温·普利布兰克称,他的父亲是粟特人,他的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的叛乱几乎推翻了唐朝的政权,然而实事、虚构与幻想的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传奇的男人。用普利布兰克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非常胖的人,极具表演天赋”,成为杨贵妃的宠儿。玄宗皇帝收到撒马尔罕等数座粟特城赠送的“胡旋舞女”后,对粟特回旋舞情有独钟,杨贵妃和安禄山都学会了跳这种舞蹈。他,一个据说至少有400磅重的男人,真的是一个穿着超大号尿布的昏乱仪式上被杨贵妃“收养”为义子的吗?
或许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传说往往比事实传播得更远。在中国的粟特人形象从异国情调和娱乐性转变为怪诞的漫画和唐朝宫廷内部道德败坏的本质。唐代粟特音乐家在骆驼上蹒跚而行的雕像是丝绸之路商队的代名词,不仅带来了西方的财富,还带来了一种放纵的气氛。甘肃粟特舞者铜像是一个头戴滑稽帽子,脚高高抬起,长着鹰钩鼻的形象;正是这种滑稽的粟特人形象流传到了旧世界的东部边缘日本。
存于8世纪奈良正仓院和法隆寺的木质面具,曾是宫廷流行的伎乐戏的配饰,用来刻画留着胡子的“醉蛮王”;这不是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可以精确定义的人物,而是一个典型的喜剧角色,体现了对甘肃舞者的视觉模仿与《唐书》中语言的那种尖锐。生活在海外的粟特人,在旧世界的东边,已经形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通过中国的视觉与语言被传达了出来。不过,考虑到他们作为小贩与工匠的地位,详实的文字记载与物质证据如此稀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来说,这些证据确实证实了粟特商人与货物曾长途跋涉,从东南亚跨越到拜占庭。对不同的艺术传统中对粟特形象的表现为粟特人的海外生活提供了不同的见证。虽然有时这表明在发现艺术品的地方有粟特人的存在,但这些表征也表明他们在创造一个"来自西域的人"这一形象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而这个形象显然为多种亚洲文化所熟知。粟特人文化身份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他们的毡帽、浓密的胡须以及对酒和舞蹈的热爱--都远渡重洋,我们可以在日本的醉蛮王面具中最清楚地看到。
但是,这个面具到底只是一个半懂不懂的、想象中的"第三人"的遗物,还是证明了粟特人在丝绸之路最遥远的边缘的实际存在,就像关于海外粟特人的许多其它东西一样,仍然是我们无法触及真相的神秘问题。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