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雕塑传统,然而在二十世纪以前,雕塑通常被视为工艺品,雕塑制作者的身份也一般是无名“匠人”。作为“纯艺术”和“艺术学科”的雕塑概念,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随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专业,与它所在的学院体制也是这一时期的舶来品。这就意味着在理解雕塑专业的建设过程时,需要将其放入“本土与外来”的框架内,但其中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元对立,因为即便是来自西方的传统,也分化出了不同的面相,而本土的民族传统其实始终参与着整个央美雕塑教学体系的构建与生长。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雕塑系教师、艺术家卢征远。

2020年11月20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精品系列展览之“雕塑基因: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雕塑教学构建中的多种传统”在央美美术馆四层展厅正式开幕。央美美术馆馆藏精品陈列项目从2012年开始,围绕中央美院及其前身北平艺专的西画、中国画、版画等专业的早期建设举办了多场专题展览。但雕塑专业由于馆藏的缺乏,其历史面貌未能以成体系的展陈得到完整的回顾。经过央美美术馆典藏部门近十年来对藏品的征集增补及整理,雕塑专业教学传统的建构过程逐渐清晰,本次展览将初步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众。多少年来也没有人专门要来考雕塑系。

本次展览以“雕塑基因”这一比喻为线索,分三个板块梳理了不同时期根植于央美雕塑系教学体系中的三种传统:来自西方的古典写实传统、苏联完善的教学体系以及中国本土的民族传统。不同的传统在央美雕塑教学体系的形成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展览通过文献、影像及相关作品的展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梳理。1928年,在这股留学潮的影响下,刘开渠与曾竹韶接受蔡元培的资助前往法国。次年,刘开渠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弟子让·布夏的工作室学习,因刻苦的态度与扎实的基本功受到赏识,从1931年开始担布夏的助手。滑田友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五艺术世界观——滑田友外版藏书之见通过滑田友藏书中的外版图书。

这段经历让刘开渠对布夏的教学理念有了更深的体会,据他回忆,布夏主张自由创造,重视独创和天才的发挥,但在基本的造型规则上,布夏仍强调写实,注重通过严谨的素描训练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而曾竹韶在1932年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转入巴黎高等美院,同样师从布夏,他在巴黎的博物馆观摩学习了大量罗丹的作品,在创作中继承了法国雕塑中富有激情的人文主义传统。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1932年和1933年,王临乙、滑田友又分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院,在专业上表现出不凡的功力与才华。两人在亨利·布沙尔的工作室学习,布沙尔以劳工为题材的作品中潜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影响了王临乙的《民族大团结》与《回到祖国怀抱》等严肃的主题创作。滑田友同样继承了布沙尔的创作理念,不断发掘古希腊、埃及雕塑中提炼造型的方法,其深刻钻研的成果得到法国官方艺术机构的高度评价:1943年的《沉思》获得了当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金奖、1946年的《轰炸》曾被法国教育部收藏、1947年的《母爱》曾被巴黎市政府收藏——上述两者的作品都在本次展览的第一板块中得到呈现。其中,王临乙、滑田友、曾竹韶等回国后赴任北平艺专雕塑专业的教师,培养出王朝闻、凌春德、司徒杰等后来央美雕塑系的主要教师力量。小马是河北大学雕塑系的应届毕业生。

1950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后,院长徐悲鸿在三四十年代以来留法归国、尤其是曾留学于巴黎国立高等院的雕塑家中广罗贤才,邀请刘开渠等回国后在其它院校任教的雕塑家北上,组成央美雕塑系第一支规模化的教学队伍。1959年,刘开渠从浙江美院调任到央美后,将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运用在课堂中,他在1960到1963年间开设的雕塑研究生班,培养了包括后来任四川美院院长的叶毓山、央美雕塑系主任田金铎在内等著名雕塑艺术教育家。刘建航院士塑像由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雕塑系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蒋铁骊创作。

在展览中我们能够看到该研究班培养的优秀学生叶毓山、田金铎、陈淑光的作品《杜甫》、《稻香千里》、《小胖》等。这些作品频繁在当时的美术杂志和雕塑作品选中刊登,反映出此时美术界对央美雕塑系教学成果的认可。新中国建立初期,虽然留法归国的教师仍在教学实践中深化法国的雕塑经验,但受到“一边倒”对外政策的影响,包括美术在内的许多文化领域,掀起了“以苏为师”的学习热潮。央美雕塑系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的教学策略,引入苏联的教学体系来指导整个雕塑系的专业建设。毕业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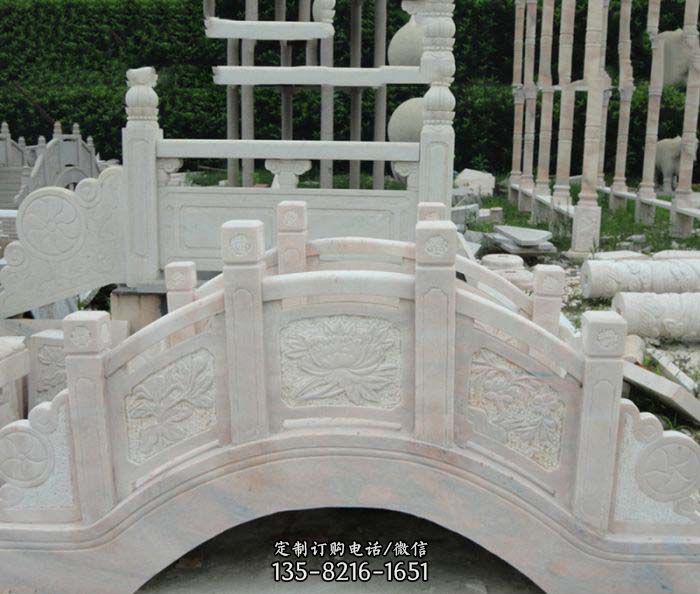
从1953年开始,央美派出钱绍武、曹春生、司徒兆光等留学生前往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经验,另于1956年邀请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老师克林杜霍夫开设了为期两年的雕塑训练班。展览的第二板块结合留苏学生的回忆录、克林杜霍夫的教学资料等文献,以曹春生的素描手稿、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毕业生苏晖的三件小型雕像作为参照来还原这段历史。钱绍武在《雕塑系三十八年历程回顾》一文中谈到了在苏联留学时的切身体会,在基本训练上,相较于法国雕塑强调形体、体积、光线的理念,苏联雕塑更注重骨骼运动、肌肉解剖结构以及整体观察、概括的能力,且在创作上要结合一定的政治需要。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

在苏晖等学员保存下来的课堂笔记中,可以看出克林杜霍夫按照苏联教学体系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每天上午进行创作训练,从头像到等身人体,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下午则强化素描和构图等基础训练。克林杜霍夫还经常带领学员外出体验生活、开展写生,培养学员的创作思维。苏联的雕塑传统虽然也源自西欧,以写实为核心,但到二十世纪中叶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出现了《普希金纪念碑》《列宁格勒的英勇保卫者纪念碑》等大型纪念性雕塑作品。雕塑系建立之初制定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均参照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教学模式。

刘开渠虽是留法一代的教师,但从1954年他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向苏联雕塑学习》一文可以看出他对苏联大型公共纪念性雕塑的推崇。他与央美雕塑系其他教员参与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和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雕塑”都受到了苏联这类创作的影响。除了艺术风格和教学方式,央美雕塑系还吸收了苏联在招生、管理和毕业考核等制度方面的经验。1958年,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的毕业答辩是中国美术教育引进苏联经验以来的首次答辩。答辩首先要求作者陈述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再由指导老师和美术理论家进行分析,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和参会者自由发言。客观再现雕塑系八十五年的辉煌发展历史。

六十年代,随着留苏教员先后归国,央美雕塑系第二代教学力量正式形成,留法留苏的两代教师共同执教,在审美观念上与社会现实更加贴近,在教学体系上也更加完备。从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前往各地美院任教,使苏联的教学经验和模式传布到全国。央美雕塑系教学从最初效仿法国,到学习苏联道路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有关雕塑艺术民族性的问题。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需要相应的民族文化艺术作为支持,央美自身的“雕塑基因”根本上还需要建立在“民族基因”之上。展现中国美院雕塑系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早在北平艺专时期,雕塑科下的“雕刻组”就开设了竹刻、篆刻、金石等传统技艺的课程,说明早期教学建设并未因来自西方的学院体制而忽略中国自身的民族传统。1935年到1936年间,中英政府在伦敦合作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据曾竹韶回忆,参观完展览后,他对中国的民族传统有了更高的认识,并立志研究和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雕塑艺术。到五六十年代,在国家的号召、教员们的民族自觉和已有教学经验的共同推动下,“向民族传统学习”也纳入到央美雕塑教学体系的建构中。自“人民英雄纪念碑考察队”之后,利用春秋两季考察古代雕塑成为央美的传统,一些古代造像还被翻制成石膏像运用在教学中。曾参与创作中山广场塑像群的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原副主任陈绳正还是记忆犹新。
在学术研究方面,王临乙、滑田友、曾竹韶、刘开渠等雕塑系教师按不同朝代分工研究,系统整理了这些古代雕塑遗存,并编辑成册,出版了《中国古代雕塑集》等重要著录。青年教员们前往各地了解学习诸如五台山泥塑、云南铸铜、潮州木雕等传统技艺,同时还邀请面人汤、泥人张、石湾雕塑的刘传等手工艺传人进入学院授课。在此基础上,央美雕塑系成立了民族、民间雕塑工作室,制定了系统的教学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展览的第三板块以王合内的作品《站立的小猫》作为结尾,这件作品造型上采用极简的线条,有一种不加雕琢的质朴感。王合内来自法国,是王临乙的妻子,在1960年正式加入央美雕塑系的教学队伍。后来考取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之后。
她从五十年代开始沉浸于动物雕塑的创作,与王临乙一同考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雕塑,其作品既具备西方雕塑精准的解剖结构,又表现出汉代动物石刻的古拙气韵,体现了来自法国与中国两种不同传统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民族雕塑传统进入教学的历史过程,不但反映了央美雕塑系师生的民族自觉意识,还使教学实践的发展经过不断的融合与再创造后,获得了更鲜活的生命力。所以美术学院雕塑系一般女生都很少。
“传统”并不意味着“古老”,回看央美雕塑系的早期建设,每一种教学传统的建构总是由青年一代的雕塑家来推动的,他们的艺术实践是当时的“新气象”,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关。刘开渠在1959年《雕塑创作的新气象》一文中评价,青年雕塑家和院校雕塑系同学在制作经验上虽然不够成熟,但他们敢于开拓创新,“我们为这些青年雕塑家的成绩而兴奋,为雕塑界增添许多新生力量而兴奋”。纵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雕塑基因”其实是一个生长的概念,如今,新的“基因”也正在被塑造着。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决定以此雕塑向四川凉山灭火英雄致敬。
改革开放后,现代主义雕塑艺术进入中国,对央美当代的雕塑教学实践同样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仍是青年一代师生的大胆实验。本次“雕塑基因”展,不仅回顾了五六十年代央美雕塑系的多种教学传统,同时也借由这段历史,彰显了先驱们在青年时代勇于开拓的艺术精神。北平艺专有记录的留学归国教师有留法的王静远、王临乙,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艺专与西迁中的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如果考虑此时的师资构成,雕塑专业的留学归国教师还有留法的李金发、程曼叔、周轻鼎以及留学比利时的张充仁、留学日本的萧传玖等。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原副主任陈绳正曾参与创作中山广场塑像群。
关于布沙尔和布夏,王伟曾在《王临乙的艺术启蒙与西学》一文有所介绍。当时的巴黎美院共有4个雕塑工作室,其中3个男生工作室的导师分别是让·布夏、保罗·朗多维斯基和亨利·布沙尔。布夏和布沙尔指导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由于两人的中文译音相似,中国学生习惯将布沙尔也称作布夏。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的许多人士经常把布夏和布沙尔两个人混为一谈。裴多菲山道尔及爱人森戴丽茱莉亚雕塑系双人半身像。
1933年,刘开渠收到时任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的聘书,于是他放弃了在巴黎继续深造的计划,回国投身雕塑教育事业,赴任当时的杭州艺专。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