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说这次疫情为蝙蝠所引发,其实,与果子狸、穿山甲一样,正因为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个蓝色星球才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科学家指出,蝙蝠携带病毒是自然选择,何况蝙蝠还是林业害虫的天敌。倘若疫病因蝙蝠而起,那么是人类贪吃了蝙蝠,还是蝙蝠侵犯了人类?地球之上,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任何种群的灭绝,都永远无法恢复。如果说唐人已经得知蝙蝠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那么宋人已经了解其觅食特点。在公民权利的历史和作品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关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地方的历史背景:年。

”岑安卿从蝙蝠身上看出其不事张扬、暗中行事的特征。前引诸诗多从其习性入手,或平铺直叙,或略加引喻,立场大多平和而中性,而在元稹诗中,则是含蓄的揭露与指斥:”他笔下的“众鸟”其实不是蝙蝠,而是某类人物,他们的危害已经不是蝙蝠感染肺炎,而已有危社稷和宗庙了。在古代文人笔下,蝙蝠更多的是负面形象,曹植的《蝙蝠赋》大概是较早的一篇:这只是一些老人们不敢杀黄鼠狼的一种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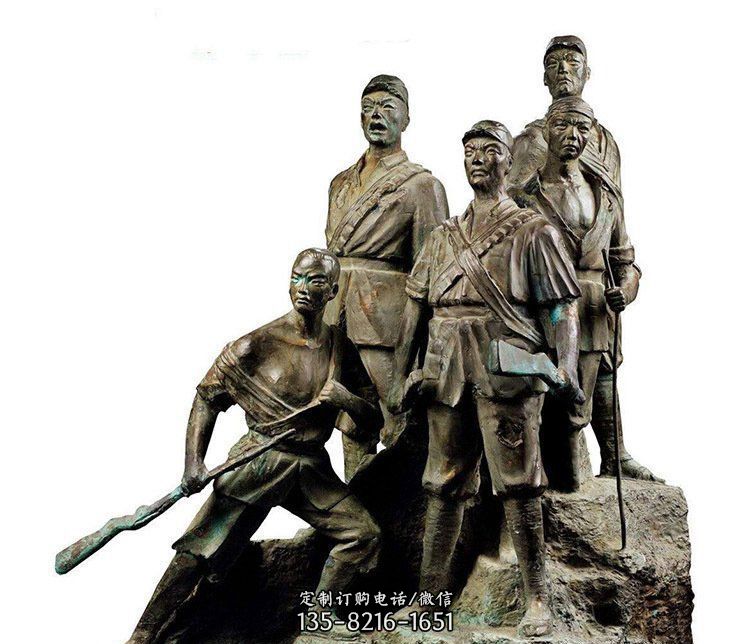
文章虽有缺佚,主体尚存,文中描述了蝙蝠的怪异习性,强调了蝙蝠的奸邪本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这正是蝙蝠另类、怪异的生理特征。文中以习性阴暗、行踪诡秘、长相怪异、角色两栖几个特点,表达了对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鬼鬼祟祟的蝙蝠类人物的批评与谴责。也许可以说,此文是以蝙蝠喻人,指斥世事,抨击邪恶的开山之作。老鼠洞黄鼠狼也能轻易钻进去。

由于蝙蝠分布的广泛性,人们借用蝙蝠特有的生活习性与生理特征,表达对某些人类情感与活动的褒贬与爱憎,在世界各地也有共通性。古希腊的文学作品把蝙蝠作为批评对象,比曹植的《蝙蝠赋》要早得多。《伊索寓言》批评蝙蝠的故事至少有两则,一是《鸟、兽和蝙蝠》,一是《蝙蝠与黄鼠狼》。蝙蝠跌在地上,被黄鼠狼捉住,将被杀死的时候,请求饶命。后来,蝙蝠又跌在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捉住,他再次请求不要杀他。因为曾经黄鼠狼这种动物的数量非常多。

在这个故事中,蝙蝠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猥琐、被动的挨打者。而在一千多年后,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笑府》中,蝙蝠则成为一个不合群的倨傲者:“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乃无奈他何!”无论被动或主动,亦不分猥琐或倨傲,在形象上,蝙蝠缺乏美感;“蝙蝠之两头无着,进退维谷,禽兽均摈弃之为异族非类也。然今日常谈,反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之人曰‘蝙蝠派’。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及其事迹的细节产生质疑。

在西方,蝙蝠始终是邪恶的象征,这有美国电影《蝙蝠》为例。但在我国,不知始于何时,至少在建筑、刺绣、玉石、工艺等领域,蝙蝠变为吉祥。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笔下形象丑陋,品质邪恶,满身病毒的家伙,到底是怎样与吉祥连在一起的?“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据说,北京恭王府的花园里有9999只蝙蝠造型的图案,加上康熙御笔的“福”字碑,正好一万个“福”字,因此恭王府又被称为“万福园”。长筒形的南瓜主要有牛腿南瓜、黄狼南瓜等。

“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虽然无论恭王府还是孟超然,都在有清一代,但邪恶之“蝠”嬗变为吉祥之“福”,并非始于清代。不过,清人蒋士铨的几句诗倒是阐述了吉祥文化的形成背景:”《忠雅堂集校笺》诗中提到的这些动植物,其实与吉祥毫无关系,只不过“蝠鹿”偕声“福禄”,“蜂猴”音近“封侯”,“戟罄”隐寓“吉庆”,“猫蝶”声似“耄耋”而已。沙狼想要捕获这些骆驼是有难度的。

就蝙蝠的文化寓意而言,西人似乎偏重于事物的本质,邪恶就是邪恶,蝙蝠很难说成什么好东西。国人偏重于事物的意象,只因“蝠”音近“福”,于是蝙蝠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吉祥物,举凡雕梁画栋、针织刺绣、玉石玩具,到处充斥着人们意淫出来的“福”气。此次疫情之初扒出的两位美女大嚼蝙蝠的画面,引发了人们的极大恐惧。其实,吃蝙蝠是“大补”,也是其来有自,《古今注》有所谓“蝙蝠…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