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便要和我们学界几万青年相见,我今天和明天两次公开讲演,要把我们欢迎他的意思先说说。讲演之前,要先声明几句话,凡伟大人物,方面总是很多的,所谓“七色摩尼,各人有各人看法”。诸君总知道,我是好历史的人,我是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人。”我今天所说,只是历史家或佛学家的个人感想,原不能算是忠实介绍泰谷尔,尤不能代表全国各部分人的欢迎心理,但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和我同感的。泰谷尔也曾几次到过欧洲、美国、日本,到处受很盛大的欢迎。这回到中国,恐怕是他全生涯中游历外国的最末一次了。看前天在前门车站下车时的景况,我敢说,我们欢迎外宾,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热烈而诚恳的。无意识的崇拜偶像,是欧美社会最普通现象,我们却还没有这种时髦的习惯。

各种意义中,也许有一部分和欧美人相同,内中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因为他从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之邦——印度来。“兄弟之邦”这句话,并不是我对于来宾敷衍门面,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不能够像地中海周围各民族享有交通的天惠,我们躲在东亚一隅,和世界各文化民族不相闻问。东南大海海岛上都是的人——对岸的美洲,五百年前也是如此。西北是一帮一帮的犷悍蛮族,只会威吓我们,蹂躏我们,却不能帮助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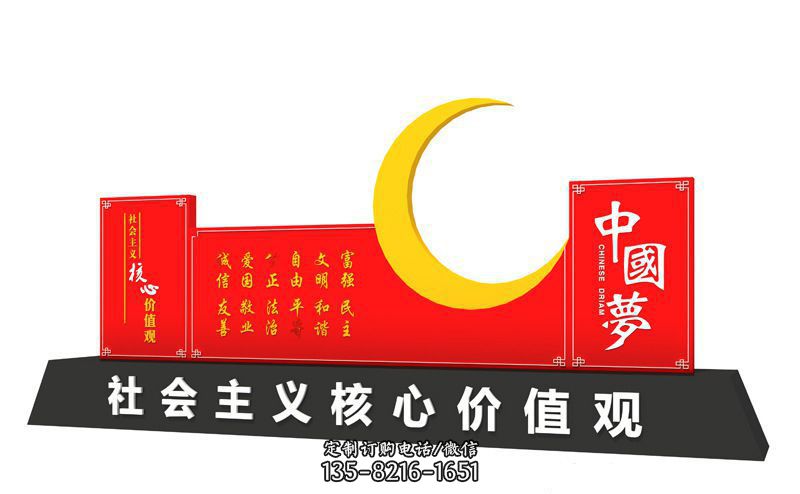
可怜我们这点小小文化,都是我祖宗在重门深闭中铢积寸累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文化的本质,非常之单调的,非常之保守的,也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他和我从地位上看,从性格上看,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儿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我们是他的小弟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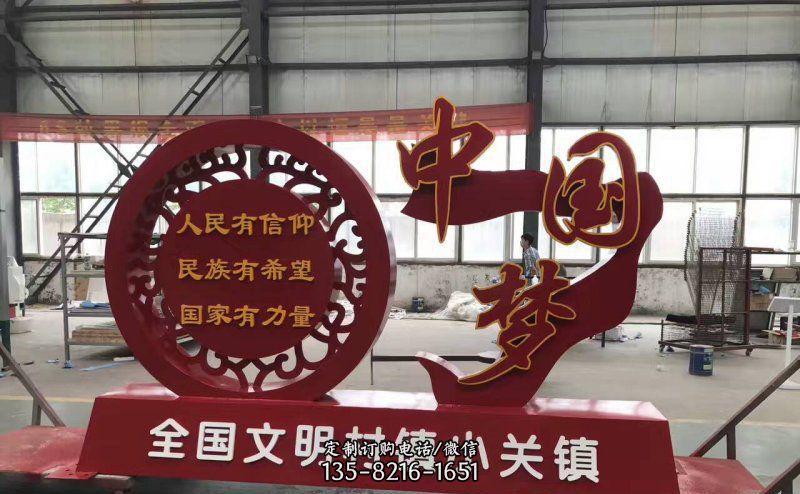
最可恨上帝不作美,用一片无情的大沙漠和两重冷酷的雪山隔断我们往来,令我们几千年不得见面。一直到距今二千年前光景,我们才渐渐地知道有您么一位好哥哥在世界上头。据他们的历史,阿育王曾派许多人到东方传佛教,也许其中有一队曾到过中国。我们的传说,秦始皇时已经有十几位印度人到过长安,被秦始皇下狱处死了。始皇和阿育同时,这事也许是真,但这种半神话的故事,我们且搁在一边。我们历史家敢保证的是,基督教纪元第一个世纪,咱们哥儿俩确已开始往来。

自从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五年——西纪六七至七八九——约七百年间,印度大学者到中国的共二十四人,加上罽宾来的十三人,合共三十七人。我们的先辈到印度留学者,从西晋到唐——二六五至七九〇——共一百八十七人,有姓名可考的一百〇五人。双方往来人物中最著名者,他们来的有鸠摩罗什,有佛陀跋陀罗,即觉贤,有拘那陀罗,即真谛。在那七八百年中间,咱们哥儿俩事实上真成一家人,保持我们极甜蜜的爱情。诸君呵,我们近年来不是又和许多“所谓文化民族”往来吗?

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土地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钱来!他们拿染着鲜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他们拿机器——夺了他们良民职业的机器——工厂所出的货物来吸我们膏血!我们哥儿俩从前的往来却不是如此,我们为的是宇宙真理,我们为的是人类应做的事业。我们感觉着有合作的必要,我们中国人尤其感觉有受老哥哥印度人指导的必要,我们彼此都没有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当我们往来最亲密的时候,可惜小兄弟年纪幼稚,不曾有多少礼物孝敬哥哥,却是老哥哥给我们那份贵重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

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患、不厌、不憎、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爱。”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中国古乐,我们想来是很好的,但南北朝以后,逐渐散失,在江南或者还存一部分,中原地方,却全受西方传来的新音乐影响。

隋唐承北朝之统,混一区宇,故此后音乐全衍北方系统。最盛行的音乐是“甘州”“伊州”“凉州”“梁州”诸调,这些调都是从现在甘肃、新疆等地方输进来,而那时候这些地方的文化全属印度系,后来又有所谓龟兹部乐、天竺部乐等,都是一条线上衍出来的。这些音乐,现在除了日本皇室或者留得一部分外,可惜都声沉响绝了。但我们据《唐书乐志》及唐人诗文集、笔记里头所描写记载,知道那时的音乐确是美妙无伦。所以美妙之故,大约由中国系音乐和印度系音乐结婚产出来。

《洛阳伽蓝记》里头的遗迹我们虽不得见,永平寺、同泰寺、慈恩寺…诸名区的庄严美丽,我们虽仅能在前人诗歌上或记录上欷献凭吊,但其他胜迹留传至今的还不少。北京城最古的建筑物,不是彰仪门外隋开皇间的“天宁寺塔”吗?北海的琼华岛,岛上“白塔”和岛下长廊相映,正表示中印两系建筑调和之美。从石刻上——嘉祥县之武梁祠堂等留下几十张汉画,大概可想见那时素朴的画风。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首推陆探微、顾虎头,他们却都以画佛像得名。

又如慧远在庐山的佛影画壁,我猜是中国最初的油画,但这些名迹都已失传,且不论他。依我看来,从东晋至唐,中印人士往来不绝,印度绘画流入中国很多,我们画风实生莫大影响,或者可以说我们画的艺术在那个时代才确立基础。这种画风,一直到北宋的“画苑”,依然存在,成为我国画史上的正统派。”中国从前雕刻品,像只有平面的,立体雕刻,我猜度是随着佛教输入。晋朝有位名士戴安道,后人都知道他会作诗,画画,我们从《高僧传》上才知道,他和他的兄弟都是大雕刻家。

此后六朝隋唐间所刻有名工妙的佛像见于历史者不计其数,可中间经过“三武毁法”的厄运和历的兵燹,百不存一,但毁不掉的尚有洛阳龙门山壁上三四千尊的魏造像,我们现在除亲往游览外,还可以随处看见拓片。其尤为世界残宝的,莫如大同府云冈石窟中大大小小几百尊石像,据说是术”的结晶作品,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处,就只这票宝贝,也足令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历劫不磨的荣誉,但倘非多谢老哥哥提拔,何能得此?
还有一种艺术要附带说说,我们的刻丝画,全世界都公认他的价值但我敢说也是从印度学来的,玄奘归赆的清单,便列有这种珍贵作品中国最古的戏曲,所谓“鱼龙曼衍之戏”,大概是变戏法的玩意儿。歌和舞自然是各有很古的历史,但歌舞并行的戏剧魏晋以前却无可考见。最初的歌舞剧,当推《拨头》一曲,亦名三万一千里南天竺附近日拔豆国传来。那戏是演一个人,他的老子被虎吃掉,他入山杀虎报仇演时且舞且歌,声情激越。
后来著名的《兰陵王》《踏摇娘》等戏本都是从《拨头》变化出来。说中国诗歌和印度有关系,这句话很骇人所闻,——连我也未敢自信为定论,但我总感觉,东晋时候译出印度大诗人马鸣菩萨的《佛本行赞》和《大乘庄严经》这两部名著,在我文学界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古诗,从《三百篇》到汉魏的五言,大半感主于温柔敦厚,而资料都是现实的。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自六朝,前此却无有。《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把佛一生事迹添上许多诗的趣味谱为长歌,在印度佛教史上力量之伟大固不待言,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
那种热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力,输入我们诗人的心灵中当不少,只怕《孔雀东南飞》一路的长篇叙事抒情诗,也间接受着影响罢!《庄严经》是把《四阿含》里头所记佛弟子的故事,加上文学的风趣,搬演出来,全书用几十段故事组成,体裁绝类我们的《今古奇观》。我国小说,从晋人《搜神记》等类作品,渐渐发展到《唐代丛书》所书之唐人小说,依我看,大半从《庄严经》的模子里镕铸出来。这还是就初期的小说而言,若宋元以后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依我看,受《华严经》《宝积经》等影响一定不少。
这些经典都是佛灭后六七百年间由印度文学家的想象力构造,这是治佛学史的人公认的,然而这些经典,中国文学家大半爱读他,又是事实。中国文学本来因时代变迁自由发展,所受外来影响或比较的少,但既有这类新文学优美作品输入,不管当时诗家或小说家曾否有意模仿他,然而间接受他熏染,我想总不能免的。这门学问,中国原来发达很早,但既和印度交通后,当然得他补助,唐朝的“九执术”便纯从印度传来,僧一行的历学,在我们历学史上是有位置的。
中国文字是衍形的,不能有跟着言语变化的弹力性这是我们最感不便的一件大事。自从佛教输入,梵文也跟着来,干是许多高僧想仿造字母来救济这个问题,神珙、守温等辈先后尝试。现存“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虽然形式拙劣,发音漏略,不能产出什么良果,但总算把这问题提出,给我们以极有益的动机和资料。中国从前书籍,除文学作品及注释古典的训书不计外,虽然称“体大思精”的经书、子书,大都是囫囵统括的体裁,没有什么组织,不容易理清眉目,看出他的条理。
自从佛典输入之后,每一部经论都有他首尾一贯盛水不漏的主义,里头却条分缕析,秩序谨严。这种译书既盛行,于是发生“科判”的专门学——把全部书脉络理清,令人从极复杂的学说中看出他要点所在,乃至如天台、贤首②诸师将几千卷藏经判为“三时五教”之类,是都用分析综合的观察,开一研究新途径。不但此也,当六七世纪时,印度的新因明学正从佛教徒手里发挥光大起来,研究佛学的人,都要靠他做主要工具。
我们的玄奘大师,正是最深造此学之人,他自己和他门下的人的著述,一立一破。这种学风,虽后来因禅宗盛行,一时消歇,然而已经在学界上播下良种,历久终会发新芽的。中国教育,不能不说发达得很早,但教育方法怎么样,共有若干种,我们不容易调查清楚,即如聚许多人在一堂讲演,孔子、孟子书中像没有看见这种痕迹。我很疑心这种讲演式的教育,是佛教输入后从印度人学来,不唯如此,即在一个固定的校舍中,聚起许多人专研究一门学术,立一定课程,中国前此虽或有之,但像是从佛教团成立以后,这种制度越发完密而巩固。
老实说,唐以后的书院,实从佛教团的教育机关脱胎而来,这种机关和方法善良与否,另一问题,但在中国教育史上不能不特笔重记。中国团体组织,纯以家族为单位,别的团体,都是由家族扩大或加减而成,佛教输入,才于家族以外别有宗教或学术的团体发生,当其盛时,势力很大,政治上权威一点也不能干涉到他。即以今日论,试到普陀山一游,便可见我们国里头有许多享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不必租界,他们里头,有点像共产的组织,又有点像“生产事业国有”的组织。
这种组织对不对,另一问题,但不能不说是在中国全社会单调组织中,添些新颖的色彩。以上十二项,都是佛教传来的副产物,也是老哥哥--印度人赠给我们的随帖隆仪,好在我们当小弟弟的也很争气,受了哥哥提携便力求长进,我们从印度得来的学问完全消化了,来荣卫自己,把自己的特性充分发展出来。方面,自己建设的成绩固不用说,即专就“纯印度系的哲学”——佛教论,天台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这几个大宗派,都是我们自创。乃至法相宗虽全出印度,然而《成唯识论》乃由玄奘集合十大论师学说,抉择而成,实是玄奘一家之学,其门下窥基、圆测两大派,各个发挥尽致,剖析入微,恐怕无著、世亲一派学问,到中国才算真成熟哩。这一千多年里头咱们两家里都碰着千灾百难,山上的豺狼虎豹,水里的龙蛇蚌鳖,人间的魑魅魍,不断地恐吓咱们,挪揄咱们,践踏咱们,咱们也像有点老态龙钟,英气消减,不独别人瞧不起咱们,连咱们自己也有点瞧不起自己了。
虽然,我深信“业力不灭”的真理,一凡已经种在人心上的灵苗,虽一期间偶尔衰萎,终久要发新芽,别开一番更美丽的境界。不信,你看曲孔林里的汉楷唐柏,皱瘦到像一根积锈的铁柱,却是阳春三月,从他那秃顶上发出几节“孙枝”,比“鹅黄柳条”的生机还充盛,咱们哥儿俩年纪虽老,“犹有童心”。不信,你看哥哥家里头现成的两位现代人物——泰谷尔和甘地。一千多年“爱而不见”的老哥哥,又来访问小弟弟来了。咱们哥儿俩都是饱经忧患,鬓发苍然,揩眼相看,如梦如寐,我们看见老哥哥,蓦地把多少年前联床夜雨的苦辛兜上心来,啊啊!
我们要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我们要搂着他亲了又亲亲了又亲…我们要把从娘胎里带来的一副热泪,浸透了他托腮上那可爱的大白胡子。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他万不敢比千年前来过的印度人,因为那时是印度全盛时代,能产出许多伟大人物,现在是过渡时代,不会产出很伟大人物。但我们以为,凡成就一位大诗人,不但在乎有优美的技术,而尤在乎有崇高的理想。泰谷尔这个人和泰谷尔的诗,都是“绝对自由”与“绝对爱”的权化,我们不能知道印度从前的诗人如何,不敢妄下比较但我想泰谷尔最少也可比二千年前做《佛本行赞》的马鸣菩萨。
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好影响,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他这回不能有什么礼物送给我们,只是代表印度人向我们中国致十二分的亲爱。我最后还有几句话很郑重地告诉青年诸君们,老哥哥这回是先施的访问我们了。记得从前哥哥家里来过三十七个人,我们却也有一百八十七个人,往哥哥家里去,我盼望咱们两家久断复续的爱情,并不是泰谷尔一两个月游历昙花一现便了。咱们老弟兄对于全人类的责任大着哩,咱们应该合作互助的日子长着呢!
泰谷尔这次来游,不过替我们起一个头,倘若因此能认真恢复中印从前的甜蜜交谊和有价值的共同工作,那么,泰谷尔此游才真有意义啊,那么,我们欢迎泰谷尔才真有意义啊!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