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者你想到的是梵高是一个精神病画家,还是他死亡案件的神秘面纱?从名人传记中发现,许多高智商的人患有精神病,如贝多芬、安培、牛顿、卢梭等,但他们大多是成名后才出现精神异常,只有少数人是在病态过程中创建成果,如画家梵高。梵高只活了37岁,离世到现在有一百多年,梵高27岁开始画画,864张油画、1037张素描、150张水彩画…不足10年的时间,他完成作品的数量之巨,着实让人们震撼。他从小自卑、自闭,潦倒落魄时的那些画作,直到死后才被人们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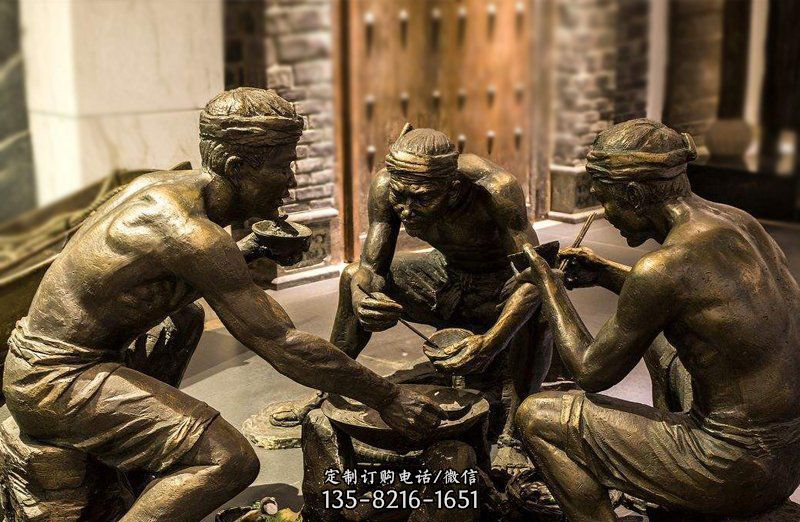
梵高的艺术潜质在小时候就体现了出来,他小时候不爱说话,沉默寡言,8岁的时候,在没有学过任何美术雕塑技法的情况下,竟然用小手捏出了一个小象的雕塑,活灵活现的,异常逼真。16岁那年,经叔叔介绍,梵高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海牙古皮尔总店的学徒工。后来因为性格直、不懂人情世故,被打压调动伦敦分店。在路过巴黎时,他看了路边不少摆摊的油画作品,对油画产生了兴趣,没想到这会成为他绘制油画的启蒙。

自那以后,他先后画了几幅油画邮寄给父母,渐渐对油画有了独到见解。1880年,梵高27岁,在经历了几年的颠沛流离之后,梵高开始走上创作的道路。临摹画家米勒的作品,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跟表姐夫学习画油,画水彩和“织工”习作,在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画,同毕沙罗、德加、修拉、塞尚相识并交往。梵高这辈子一直在接触底层,他经了世道的不平和生活的艰辛。他深深地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强烈地希望自己能够有力量去解救他们。在他当传教士的时候,就曾经把自己的钱财和衣物都拿出来接济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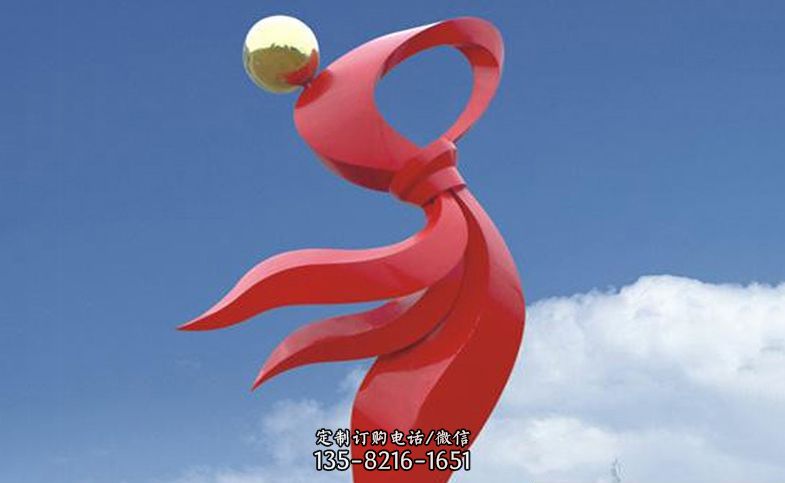
他经常深入到劳动者阶层,和他们交流情感,了解他们的生活。梵高有意识的强调色彩,一些传统的艺术效果被他有意忽略。他绝不故步自封地照搬传统和照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终身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发明出了属于本人的艺术风格。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苦楚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

梵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当时梵高刚开始自己的创作,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代表的艺术风格还没有被世人认识和理解,他的创作不被别人认可,作品没有销路,但是梵高仍然坚定地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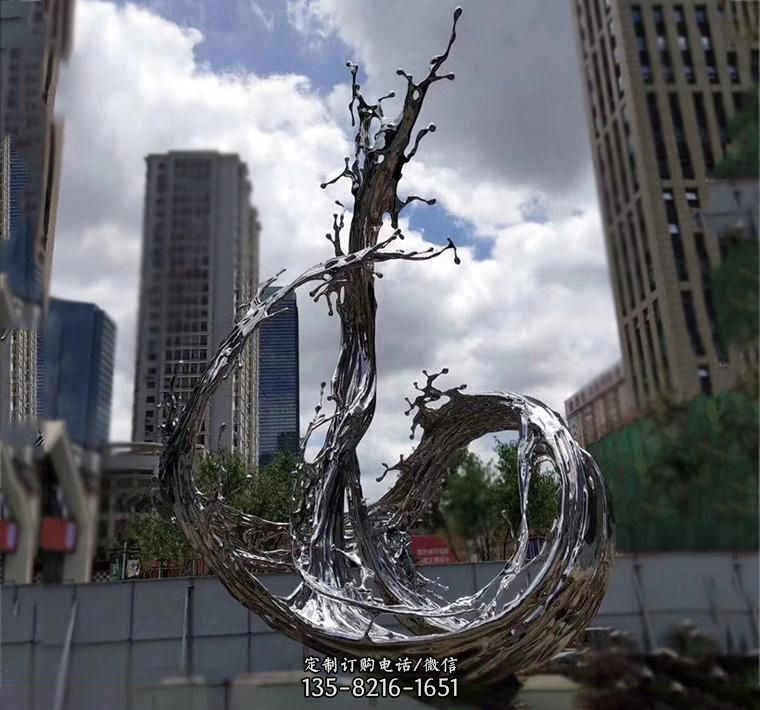
梵高的那时候早已抛弃了再现真实的这种绘画风格,他已经痴迷于自己恣意挥洒是色彩和粗狂奔放的绘画笔触,陶醉其中,难以自拔,并没有考虑大众们还滞后的欣赏能力,也没有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绘画被大家接受。对于那些,以再现客观现实为标准的人眼中,梵高根本就是个不会画画的人,更别说买他的画了。在别人对他不认可这段时间中,梵高无比的压抑、悲观,从而使自己患上了精神病。梵高一生穷困潦倒,他时常忍饥耐寒,将仅有的生活费用拿去买画布和颜料,他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弟弟的不断资助来维持,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弟弟的累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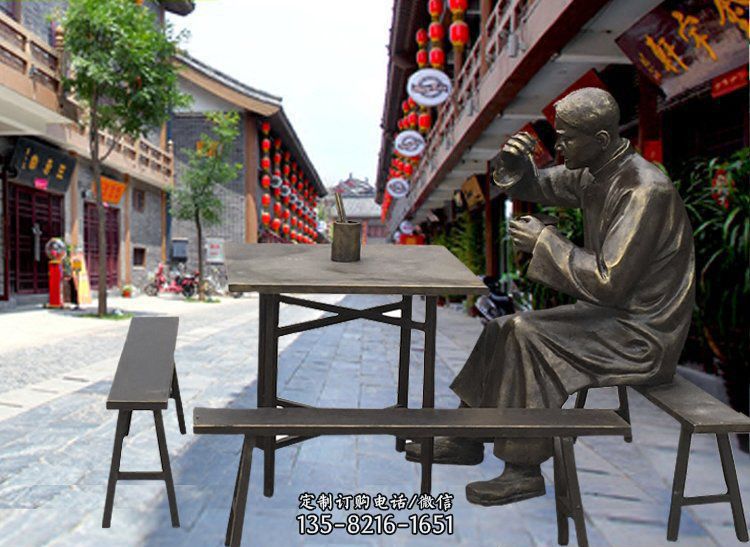
1885年到1890年期间,梵高创作出了大量油画作品,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们》、《向日葵》、《星夜》、《麦田上的乌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时,评论家开始评论凡高,并卖出了人生中唯一一幅画,他非常高兴地去跟自己的弟弟说,我终于卖出去一幅画,实际上这幅画就是他弟弟出了钱,找一个人当托儿来买的。梵高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天才,他甚至不敢把自己称作画家。提奥,从不间断地、无私地为梵高提供经济资助,提奥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梵高的人,他们之间有几百封的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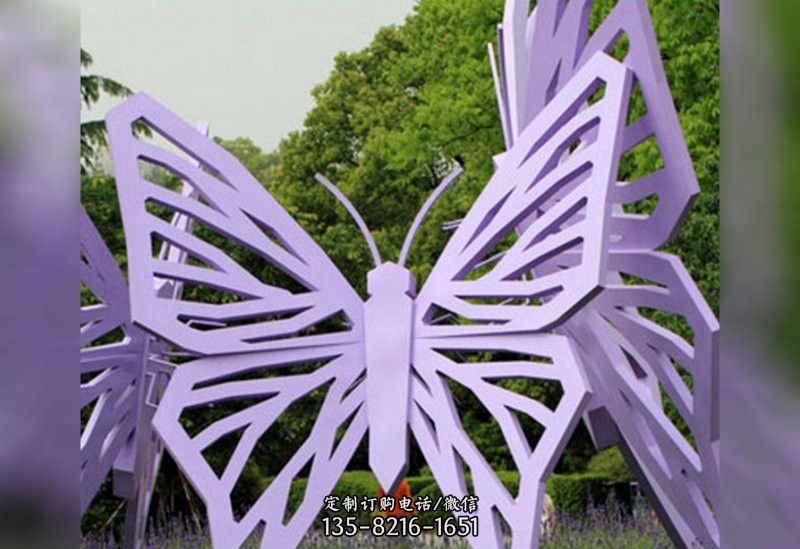
1890年,梵高在巴黎附近奥维尔郊外朝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有人认为,梵高是被几个男孩误伤,善良的梵高为了掩盖他们的错误,说成是自己开枪。原因是梵高在之前仍然保持着很积极乐观的创作,并且写信让他弟弟寄来颜料。1891年1月,梵高死后六个月,相随他一生的弟弟提奥在悲痛中过世,死时只有33岁,医生说:随后,提奥的妻子乔安娜在抽屉里发现了他们的通信,乔安娜本来对梵高并不熟悉,但当她读过梵高的信,被深深的触动了,也被梵高的人生和创作所深深吸引。

从此,乔安娜通过自己勤奋、智慧的工作,一步一步使世界了解了梵高。她经常将梵高的作品借出展览,后又开始整理那些浩繁的书信。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整理并发表,还为梵高的作品举办画展。可以说多亏了她的努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梵高的作品。我们熟知的梵高的《星月夜》这幅作品目前存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虽然未在市场上销售过,但是很有潜力成为梵高最贵作品的前10之一。梵高的作品由于具有生动、丰富的色彩和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其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印象派画家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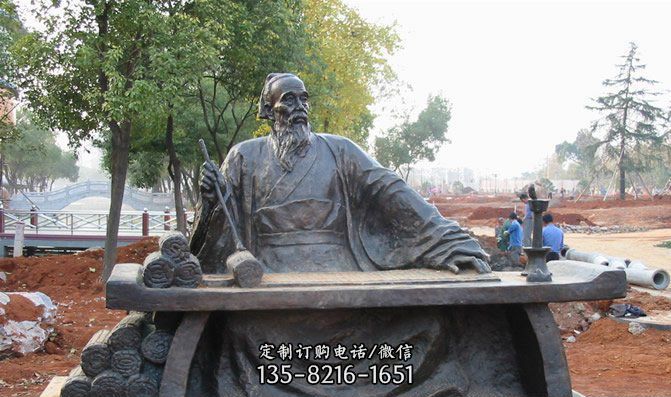
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