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看来,雕塑正是一种让时间停止的尝试,人们希望借雕塑跨越时间,已达永恒,而雕塑又借时间获得内涵、趋于完美,“我们沉浸在空间里,也沉浸在时间中。正是因为雕塑的这种特殊内涵,它往往与死亡结合在一起,人们用自己的雕像抚慰生命的短暂,用亲人的雕像告慰死亡的痛苦,又或用千军万马的雕塑,冲散对死亡的恐惧。《雕塑的故事》一书辑录了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与艺术史学者马丁·盖福德关于雕塑多个面向、多个维度的对谈。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其中《时间与死亡》一章,图片为原书所有。想想现藏大英博物馆的拉美西斯二世像那巨大的头颅和身躯,要用铜制工具和砂石打磨出如此完美无缺、严丝合缝的表面,所花费的时日想必是惊人的。我们今天有各种先进的镀钛工具,却远远无法表现出雕塑表面那种清晰可见的张力。我的作品《别处》,部分放置在英格兰默西赛德郡的克罗斯比海滩上。这些铁制的人形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表面被藤壶缓缓占据,有些已经完全布满藤壶。

整件作品安放在一片长约3.2千米、宽约0.8千米的区域内,有些人像之间还有流沙。我们在安装作品时,有好几次差点连安装设备都丢失了。它正渐渐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存在于时间与季节的更替之中。其实那些藤壶至关重要——雕塑遇到的偶然情况都很重要,它们是作品与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艺术家本人是否愿意,时间都会对我们看到的艺术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你甚至可以将时间看作不请自来的合作者,几乎总要掺和进来。

最初,人类将一块岩石或金属塑造成形,随后,成百上千年的时光将其再度改变,风、霜、地震乃至种种意外都发挥着作用。不同于门农巨像,拉美西斯二世像的皮肤依然坚硬光滑,但是他早已破裂倾倒。雅典帕特农神庙西侧的山墙上,曾经斜倚着一尊大理石雕刻的河神像,很可能是伊利索斯河的河神。尽管他的头颅、左手、右臂和双脚都已不存,身体姿态与肌肉线条却还保存完好。他的皮肤有些地方已经深受侵蚀,看起来不像大理石,倒有点蕾丝织物的质感。这件雕像仿佛正在缓缓溶解,就像分崩离析的崖壁,所以你能轻易透过表面看到内在的质地。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雕像与古代雅典人所见的样子迥然不同。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件艺术品比以前还复杂、还迷人呢。

这件作品,让我们透过表面看到内部的物质实体,由此感受到我们自身的弱小与身处的险境。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更希望岩石的质地能够显露出来,而不是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像那样表面加工得极其精巧完善,比如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尔墨斯》——存留至今的古代雕塑中,唯一一件可以断定其作者的大师之作。时间总是或多或少地提供新的解读方式,而且往往与原本的宏大设计背道而驰。

大自然能够持续加工一件雕塑,而且有益无害—我很喜欢这种看法。罗丹生前收藏的这件《撑立的赫拉克勒斯》就是一个绝妙的例子。作为一件石制的物体,在时间的作用下,它重新与自然合而为一。为了参与自然的无序化进程,这件作品具象写实的一面被牺牲掉了。这正是日本思想中所谓“侘寂”的概念,即假人类之手造出的东西可以与自然和时间的造物相互交融—少一分执着,多一分融通。

罗丹生前的工作室兼住宅坐落在巴黎城外的小城默东,你如果到此参观,就会发现他曾以许多古代雕塑残件为伴。他显然认为这些残缺的作品能够传达重要的信息,既能教给他雕塑艺术的追求,也能让他明白雕塑终究难逃腐朽的处境。当然了,后世的艺术家见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绝不是簇新的,而是经历了数千年风霜保存下来的残件。漫长的岁月使雕塑改头换面,却往往能够给艺术家带来灵感。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米开朗琪罗,他曾见到一件被称为《望楼的躯干像》的作品,原本是某个英雄人物的雕像,已经残损得只留下一个躯干。尽管这件雕像肢体残缺不全,甚至刻画的是哪个古代英雄或神明都无人知晓,但对米开朗琪罗而言,其魅力有增无减,意味无穷。据说米开朗琪罗曾劝说教宗不要将其修复,他本人也拒绝承担修复工作。

得益于米开朗琪罗的大力颂扬,《望楼的躯干像》在16世纪声名鹊起。我们对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在他生前有一位年轻的作者出了一本书,书中提到了这件事,而这位作者很可能与他过从甚密。大师从这件作品中学到了很多—原来肌肉发达的人体能够如此生动地表现活力与挣扎。但是就算没有这个记载,我们也能理解这一点,只消抬头看看西斯廷礼拜堂的穹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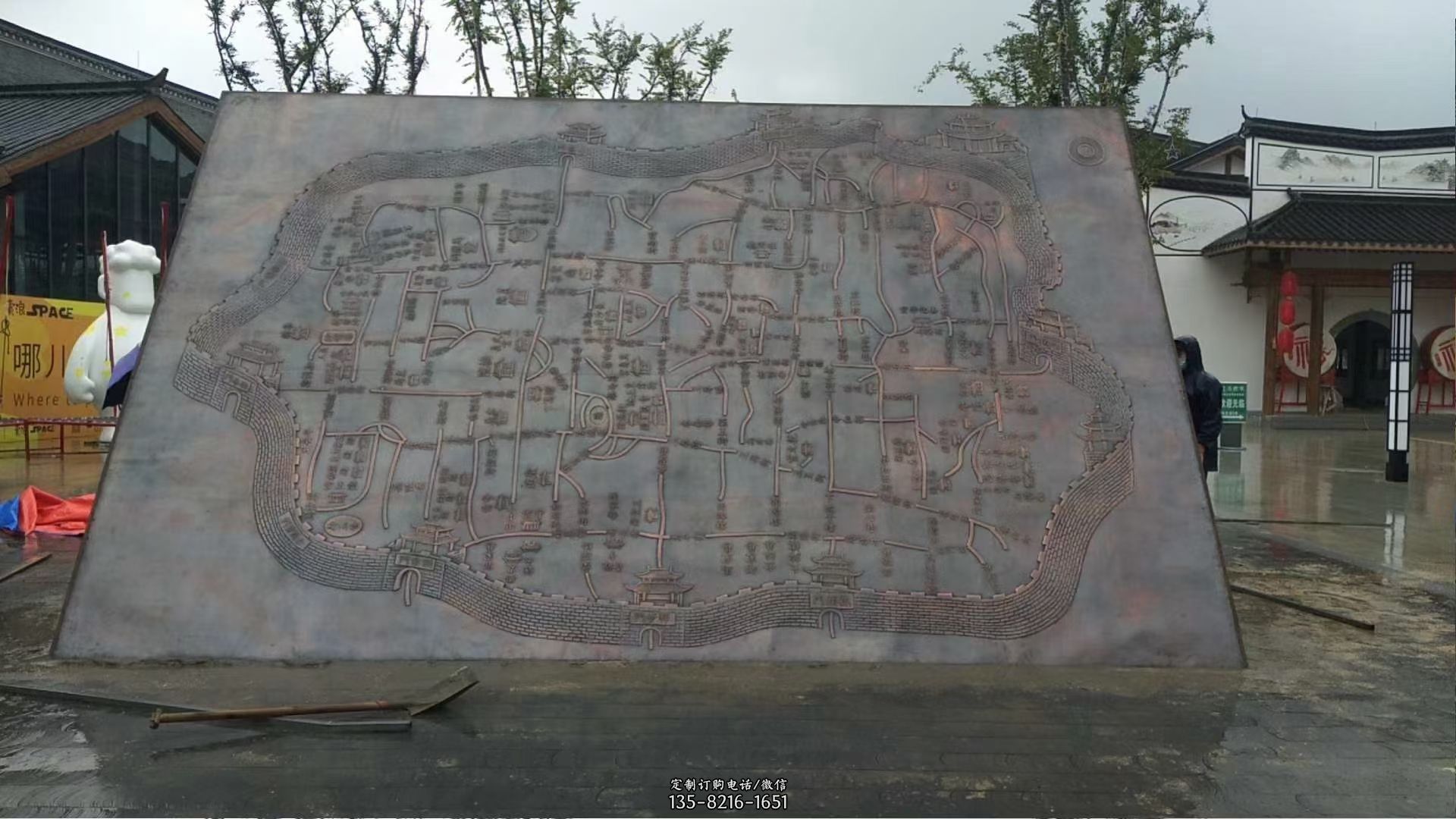
《望楼的躯干像》确实教会了米开朗琪罗如何在雕塑中运用肌肉,不是吗?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残躯使用的石材,这凸显了它作为一件物体的物质性。与此同时,它又是用石头刻出来的人像,需要你的参与才能扩展完善。要检验一件雕塑的优劣,只需将其从山顶扔下去,如果一路滚至山脚下仍然还像一件雕塑,说明是件好作品。这件残躯看起来就像曾经参与过类似的严酷考验,而剩下的则是它不可磨灭的精髓。你终有一死,但是你的形象会留存下来—只要别让什么东西给毁了就行。

然而经历千百年保存下来的也许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刹那,这未免有些矛盾。贝尼尼为希皮奥内·博尔盖塞主教所作的两件半身像,看起来仿佛是电影的定格画面—以无比精湛的技巧在大理石上雕刻出来的定格画面。就像多纳泰罗的那件《先知哈巴谷》一样,张开的嘴巴能够让一件肖像富有生气,同时也有点诡异。这位主教虽然是用石头刻成的,但仿佛要开口说话一般。事实上,他看起来好像已经口若悬河地说了半天,以至嘴角都泛起了涎沫。

这个嘛,我倒觉得贝尼尼不大可能真有批判的意思,毕竟博尔盖塞主教是他最重要的赞助人,而他终身都为教廷服务。主教本人很喜爱这两件半身像,但是我们今天看来,他确实没有一点虔诚基督徒的样子。有一次贝尼尼故意做出一副疯狂的表情,张大了嘴巴尖叫连连,以此来模拟地狱中受苦的灵魂。这可能是一种精神的练习—圣依纳爵·罗耀拉建议他只需运用想象的眼睛来幻想地狱中的苦难—也可能是雕塑家的玩笑,艺术家将自己在镜子中做的鬼脸永久地保留了下来。
与他相比,弗朗茨·泽维尔·梅塞施密特所作的一系列《怪人头像》,虽然也是根据自己在镜子中的鬼脸创作的,却是一个真正饱受折磨的灵魂的自画像。梅塞施密特早年是一位颇为成功的晚期巴洛克风格雕塑家,虽然有点呆板,但心智想必是正常的。他曾为维也纳的许多要人造像—当时正是玛丽娅·特蕾莎女王在位,权贵都戴着假发—艺术水平相当高。有人造谣说他精神状态不稳定,以致他没能成为维也纳美术学院的雕塑教授。此后他退居外省,并创作了这一系列的雕像—原本共有170件,现存69件。在这些雕像中,他把自己的五官扭曲成生理条件所允许的最疯狂、最极端的表情。
梅塞施密特解释说,其中一些头像表现了“动物的超自然感觉”,有两件是为了对付一个晚上纠缠他的恶灵而制作的。而在他的作品中,被社会秩序压抑的恐惧与狂躁情绪,仿佛在一瞬间全都释放了出来。这组肖像不禁让我们思忖—在这些流传后世的作品中,艺术家究竟保存下来了些什么?就梅塞施密特而言,他留给后人的是焦虑和骇人的妄想。一件肖像之所以富有表现力,正是因为经过了提炼,去除了那些让人分心的成分。创作肖像不仅要追求形似,还要判断哪些元素是重要的—要对人的面貌特征加以取舍,以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你眼中的这个人物的特点。
我曾到维也纳美景宫博物馆观赏这些头像,当天还去了疯人塔。疯人塔是旧时的一座精神病院,展示着种种治疗肺结核与精神疾病的残酷实验。梅塞施密特的作品,仿佛是试图将人内在的精神状态进行分类—古典雕塑也讲究人物动作要富有寓意,但他的探索远远超出传统的范畴——似乎预示了后来法国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沙可在癔症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心理疗法与精神分析的开端。
而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冲动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怀疑代替确定,用焦虑代替安稳。我从小所受的教导让我畏惧上帝、畏惧父亲、畏惧失败。有时我的创作近乎一种疯狂的仪式——努力让某个时刻变得有意义,为物质赋予情感。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内那尊为诗人、牧师邓约翰所作的纪念像,大概与贝尼尼生活时代相当。这座雕像可以说是一件请人代为雕刻的自塑像,因为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是邓约翰本人想出来的。
17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艾萨克·沃尔顿1640年出版了《邓约翰传》,记述了这段逸事。他找人做了一个木制的骨灰瓮,自己身披裹尸布,站在瓮上,摆好造型,让一位“精心挑选的画家”为他画像。他的书房里烧着炭火取暖,故而这位大诗人虽然只裹着一层单子,倒不至于受冻。他站在那里,双目紧闭,面朝东方—他认为最后的审判到来之时,基督会在东方现身。
邓约翰在1624年写下了著名的布道文《突变引起的诚念》:”似乎写作此文时,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死时的情状。画作完成之后,诗人将其放在自己的床边,时常端详沉思—就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前一样。邓约翰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让雕塑家根据这幅画制作了一尊大理石雕像,放置在他的坟墓上,这大概是诗人自己的意思。1666年伦敦大火,圣保罗大教堂被焚毁,只有这么一件塑像保留了下来。据说,它像一颗导弹似的穿过地板掉了下去,人们随后在教堂地下室发现它时,竟然完好无损。
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他居然如此精心地为自己安排身后之事。但是他的两只眼睛实际上都微张着,仿佛在思考着自己的死亡和即将来临的复活。他身上的布料看起来湿漉漉的,表面平整,周身轮廓十分简洁,再加上头顶那个用布料折成的冠冕,整体感觉十分奇异。而他那长满髭须的脸上又挂着一抹微笑,犹如贝尼尼的那尊《圣女大德兰的神魂超拔》,仿佛也处于一种精神入迷的状态。雕塑从来都在探讨生与死的界限,或者说我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
在各种丧葬形式中,举行丧礼的人都会对死者的遗体致以尊重与哀悼,这个备受重视的死者往往是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最早出现的雕塑性质的物件就与这种仪式行为息息相关,我对其中的关系很感兴趣。秘鲁和智利的木乃伊可谓是用真人骨骼作框架制成的雕塑。这件新克罗木乃伊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将人的身体当作一件容器,嘴巴洞开,里面一片漆黑。南太平洋的托雷斯海峡岛民也用死者本人的头骨制作面具。
新几内亚的塞皮克人和阿斯马特人也会用死者的头骨来制作肖像。在这些传统中,艺术作品与其表现的主题之间的界限瓦解了—它就是它的所指。古罗马人倒是不公开展示祖先的头颅,但是他们有一种十分相似的做法。这种用真人翻模制作的头像,保留至今的可能只有一件。但是据说他们宅邸的门厅里摆满了这种面具,所以每个走进门的人,都要面对成群结队的祖先——这种陈列意在使祖先不朽,但未免有些恐怖。
在送葬的队列中,也会有一个与死者身材非常接近的人戴着这副死亡面具走在人群中。这些真人面部倒模想必为古罗马的石雕肖像树立了精确度的标准,很可能也直接成为参照。罗马石像中的佼佼者之所以如此逼真动人,也就不难理解了。古罗马的头像,就好像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画穿越到了两千年前。这些雕像毫无浪漫主义气息,却将一个曾经活在世上的人的外表和性格完整固定下来,供后人瞻仰。在全世界的多家博物馆中,你可以纵览古罗马帝国整个皇族——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与妻子莉维娅,第二任皇帝提比略,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乌斯,等等——仅从这些雕像就可以了解背后的历史。
你能认出哈德良,尤利乌斯·恺撒的秃脑瓜也很好认,还有卷头发的马可·奥勒留。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门答腊岛的长屋顶上挂的真人头。两者的区别在于,这些古典肖像完全没有宗教意味,它们的旨趣仅限于心理层面——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古罗马肖像雕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全然接受人终有一死的宿命,试图抵抗,但又勇于直面它。我对这些塑像情有独钟,因为它们只如实记录死者的性情,无论男女,绝无任何理想化的倾向,如此恒定。他们追求令名、美德,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严格约束自我,目的都是为家庭和邦国服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肖像雕塑被置于死者的坟墓之上。
所以人虽然死了,他们的鲜活形象却保留了下来,有的能保存数千年之久。我很喜欢在爱琴海米科诺斯岛的博物馆中见到的那些墓碑——死者与生者握着手,仿佛永远都在道别。没有装腔作势,没有无病呻吟的象征符号,没有天使也没有挽歌,不过是生者与死者的道别,简简单单。同样是面对死亡,中世纪的丧葬雕塑则反映出了一种与上述迥然不同态度。我在约克郡艾姆培尔福斯求学期间,经常听爱德华神父讲解14世纪的丧葬纪念雕塑,遂对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和英国墓葬雕塑产生了兴趣。
这一时期,他们的坟墓上通常有两件雕塑,上面是衣冠整齐的墓主人,下面则是正在腐烂的残骸—同样的一具躯体,只是后者正在被蛆虫啃食。位于牛津郡的尤尔姆教堂安放着萨福克女公爵爱丽丝·德·拉·波尔的陵寝。上方的石像是她生前的形象,下方一道透雕格栅后面安放着第二座雕像,表现的是她死后的形象。我很喜欢第二座雕像,它刻痕很深,因而实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形式效果,比如头发之间的空隙,以及脖子上的裂纹。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为纪念幼子彼得所作的这件雕像《举哀的父母》,位于比利时,也许是父母怀念子女的雕塑作品中最为感人的一件。
彼得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他到达前线不过几天就殒命沙场。这不仅仅是一位悲痛万分的母亲创作的作品,也是艺术家本人对骇人苦难的回应。她用了将近十八年,才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雕像中的柯勒惠支与丈夫双膝下跪,朝向埋葬着自己幼子的这座战争墓园。在《举哀的父母》中,两个人的身体正在努力控制住内心的情绪波动,而艺术家使用的塑造手法却十分微妙:男人的双手紧紧环抱着自己的身体,努力克制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巨大痛楚,这双手又与其硕大的头颅相呼应。
他们身上并没有《邓约翰纪念像》中的那种超拔,只有跪伏在虚无边缘的无尽悲戚。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