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雕塑,第一时间浮现心头的可能是那些巨大的、栩栩如生的人像,它们或作沉思状,或停滞在掷铁饼的前一瞬间,或断了半截手臂,却仍然以惊人的美丽吸引着人们。一个雕塑作品可能蕴含着无数天才的想象与艺术的灵思。今天分享当代著名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和艺术史学者马丁·盖福德关于著名雕塑的部分对谈,节选自两位的对话体著作《雕塑的故事》。我们智人最重要的能力也许就是想象力,换句话说,就是构想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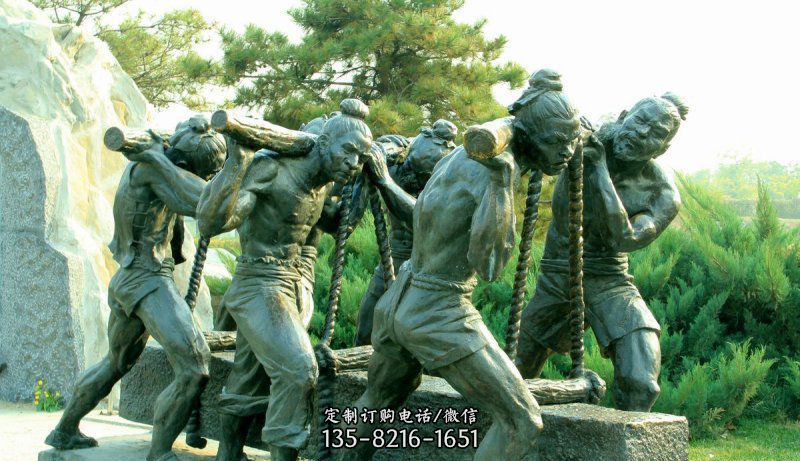
赫拉利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灵长类近亲,正是因为具有不断进化并相信集体想象的产物的能力。他举了许多例子,比如金钱和法律,它们并非客观存在的东西,尽管都可以用实在的事物表现出来。就像《彼得·潘》里的小仙子一样,只有人们相信,它们才能存在。具象绘画和雕塑同样是想象的产物,它们表现的可以是不存在的事物,比如狮人和拉玛苏都是子虚乌有的。

同样地,至少对不信宗教的人来说,所有表现神明或神话的雕塑和图像也都是如此。但是,最有趣的作品并不仅仅表现“集体想象”,还体现为根深蒂固的身体观念,以及对其他动物身体的移情。在有些地方的史前洞窟里,洞熊会在穴壁上留下抓痕,后来某个智人轻描淡写地添了一笔,这些抓痕就变成了猛犸象的鬃毛,真是妙不可言。在洞穴艺术中,你能看到人类与空间中的其他动物一道,和生存搏斗的最初尝试。

从本质上来说,洞穴壁画,比如鲁菲尼亚克洞穴中描绘的这只猛犸象,表现的是对我们本性的深刻思考。对我而言,这些岩画至今仍是对“艺术何为”最好的诠释——艺术是连接想象与现实的纽带。不过,赤陶也可以用来制作形制较大甚至真人大小的作品。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为独特也最具野心的一项雕塑工程,正是以黏土烧制成的,就是护卫着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1974年,西安城外西杨村农民在凿井时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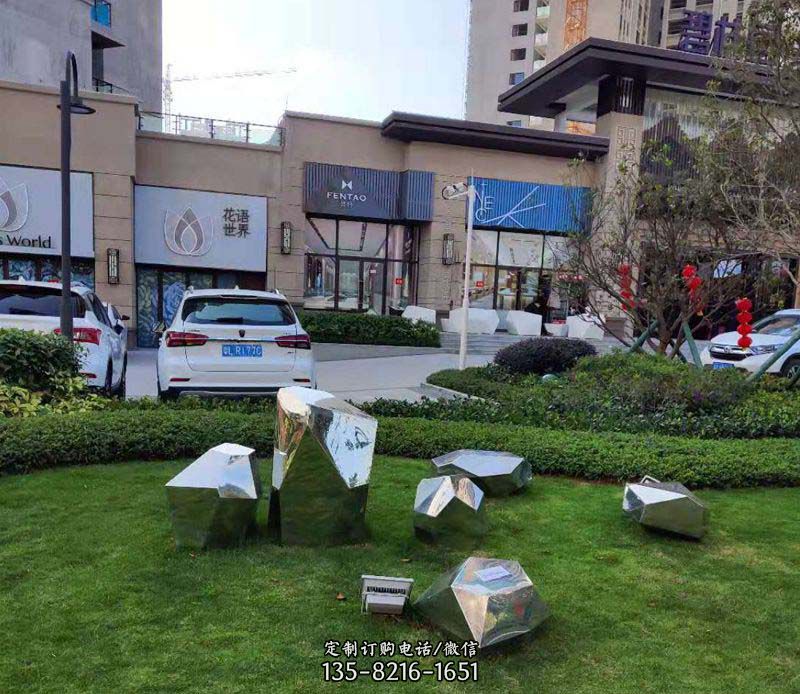
后来,当地的官员来此视察凿井进度,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叫停。此后,这里出土了千余尊陶制兵俑,而整座遗址中出土的兵俑数量有七千余尊,还有五分之四尚未发掘,静静地埋藏在土中。兵俑均为真人大小,数量众多,差不多抵得上一座小城的人口。他们排成整齐的行列,仿佛一众亡灵刚刚从地下大踏步走出来,庄严肃立,等待着下一个命令。其中还有成队的陶马,它们原本拉着战车,可惜车身早已朽烂,只留下了金属配件。沿着俑坑四周漫步,你会发现有些陶俑还是刚发掘出来的样子,歪倒在地,破碎支离,莫名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战壕里拍的那些老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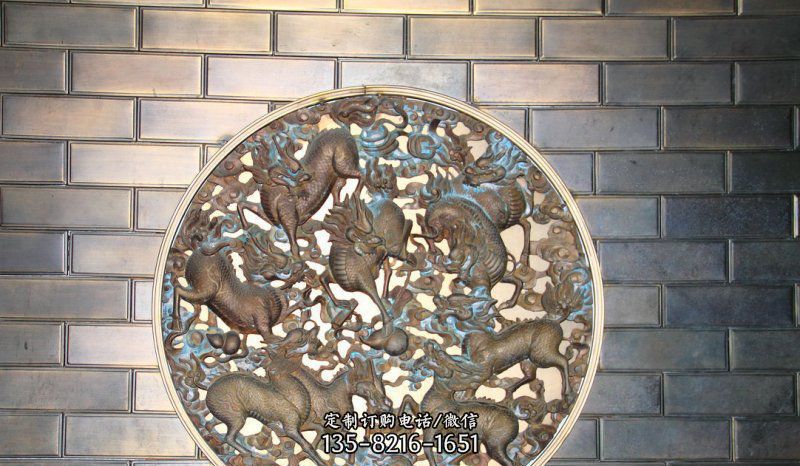
在俑坑边沿还能看到一些圆形凹痕,这是因为坑道上方曾经横跨着巨大的梁木,梁木之上填埋泥土。如此看来,在诸多事物中,兵马俑也是黏土耐久性能的一个有力证明。兵马俑就被放置在孕育他们的土地之中——对我而言,这正是它们的部分魅力所在。它们许多还是刚被发现时的样子,残缺不全,半埋在土地里,前面的部分从土中涌现出来——重获力量,精神勃发,好似复活——看起来美不可言。

可以说,雕塑的制作,堪比基因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人体。仅仅是制造这样一支仿真的军队,已经是一件组织严密的壮举了。考古学家发现,制造兵马俑的工匠分为一个个小队,由各自的工长率领,工长则听命于级别更高的官员。管理兵马俑制作的系统,堪比实际统帅秦始皇兵马的官僚机构。假设每名工长下辖十来个人,那么受命制作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工匠少说也有上千人。所以说,黏土看似平平无奇,竟然能造出规模如此宏大的雕塑群。

我在剑桥读书时,每次到菲茨威廉博物馆,都会对《塌鼻男人》的青铜复制品点头示意。菲茨威廉博物馆向来以优雅著称,这里收藏着乌兹别克斯坦著名的布哈拉地毯和红锆石,四处弥漫着家具抛光剂的味道,而《塌鼻男人》身处其中显得十分突兀。与其说这是一件人像,不如说是一件物品——一个脸上写满了无言的历史的男人,既像苏格拉底,又像法国小偷兼哲学家让·热内,让你过目不忘。《塌鼻男人》看起来像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东西,放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合适。

1863年秋天,刚刚二十出头的罗丹开始为这个面部受损、一脸沧桑的中年男人塑像,有时一天连续创作五个小时,直到1865年春天才告完成。有一天晚上,用黏土塑造的比比头像受了冻,头后掉了一大块。这次意外反倒引起了罗丹的强烈兴趣,他干脆就将只有面部的头像送交一年一度的巴黎沙龙评选。我曾在菲茨威廉博物馆见到青铜的《塌鼻男人》,和绝大部分大型青铜作品一样,它也是中空的。这件作品是用原作翻模制成的,来自活生生的人,但是由彼到此,经历了一系列的步骤,每一步都要用到专门的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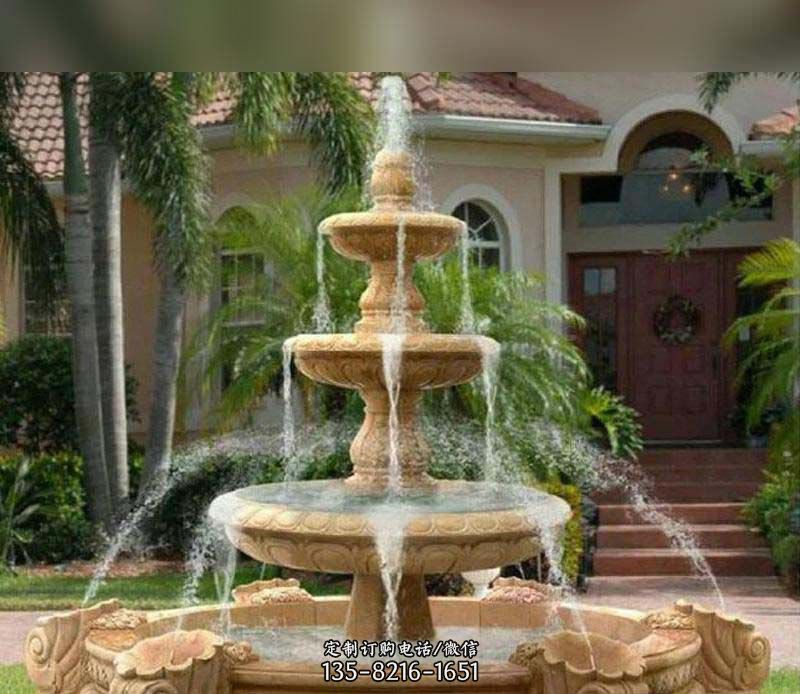
用青铜来浇铸雕塑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原件经过多次翻模,才能成为眼前的成品,而那件被冻碎的泥塑只是第一步。这并不是一张模式化的脸,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却有着真实的情绪。其面部特征——茫然的双眼、布满深纹的额头、塌陷的鼻梁、紧闭的嘴——给人一种游移不定的感觉。尽管他一生的艰辛往事都被刻在了五官中,这个高贵的个体仍然一脸迷惘——默然无语、无处容身,而且不被理解。

但矛盾的是,这不过是一副面具罢了——绕到它后面看,就会发现里面是空的。奇妙的是,认可了青铜带来的错觉,反而让这件作品更有力量了。一切的收藏和展示都是如此——所用的材料不一定是罗马城市雕塑残块,而可以是任何东西。作品范围的拓宽,得益于20世纪初杜尚富有智慧的实践。他着眼于所谓的“现成品”,即日常所见的工业化产品,包括雪铲、小便池和自行车轮等,并将这些东西重新定义为艺术作品——他的艺术作品。
杜尚的神来之笔,是将这些物品从时间和现实的商业交易中抽离出来,把它们放入艺术馆的建筑空间中,还往往展示在玻璃柜里。这种胡言乱语似的东西之所以能成为作品,完全是基于既有的博物馆概念,以及艺术家作为思想者和文化规范批评者的自我意识。杜尚主张,艺术的关键并不在于从大理石中提炼出一个理想化的物件,而在于你做出的选择。确实,我们在思考杜尚和他的艺术策略时,不能脱离这样的背景,即博物馆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分类和制度。
艺术品不再是简单的圣像、纪念碑或偶像,而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从供人欣赏的客体变成了独立的主体。换句话说,“什么是艺术品”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而问题的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一个关键人物,他将什么可以是艺术、什么又不能是艺术的问题,摆在了当代艺术讨论的中心位置。他意在引导我们思考——如果一样东西被视为艺术品,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虽然如此,我对杜尚作品的感觉和你对卡诺瓦作品的看法相同。
除了少数例外,杜尚的作品在我看来都很枯燥,毫无生气,看不了多久就会厌倦。但是我对他的感觉,就像曾经的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质疑对手提出的政策时提的那个问题:我坚信杜尚有一点说得没错,那就是如今的艺术要靠观者来完成一半的创作。事实上,他使用现成品就是要让我们一同参与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而这是无法预先设定的。但是在我看来,其他人基于杜尚的思路创作的作品,往往比杜尚自己的作品震撼得多。就拿杜尚的《自行车轮》来说,这是他作品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件现成品,严格来说是有辅助的现成品,因为他把车轮和一个矮凳组合在了一起。
作品的效果十分简约典雅,但是这并不是一件蕴含情感与意义的真正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个示意图——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杜尚要求我们在这个人工制造的世界里,透过艺术的表象看到我们自己。当它出现在“现成品艺术”中时,就有可能让我们将一切人工制品都视作无意识的象征对象。他的《自行车轮》将日常生活中的两个物件组成了一个综合体,看起来简洁优雅。
但是我从杜尚那里看不到任何对人类历史的解读,也看不到作品与未来的联系——无论这个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乌托邦,还是充满焦虑的世界。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