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堡垒”的展厅略显空寂,在当代艺术界享有盛名的马修·巴尼对于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似乎略显陌生。在“堡垒”一展中,马修·巴尼放弃了以往作品中迷宫般的叙事和华丽的视觉奇观,呈现出一片荒芜的肃静,使作品与观者之间保持着某种难以逾越的距离,或许让习惯了通过体验来认知艺术的现代观众难以捕捉到较为直接的感受或可交互的信息。艺术家以神话为叙事蓝本,依循美国爱达荷州的自然景观及对狩猎活动的描述,通过近十个主题,展出了约50件金属装置及一部与展览同名的影像作品。

尽管巴尼不断强调“材料、叙事和意义的杂合”,但散布在作品中的纷杂意象依然提供了诸多可供解读的途径。近30年来,马修·巴尼无疑是当代艺术界炙手可热的宠儿。“使用了他的前辈们无法获得的艺术资源,并孕育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全部视觉艺术。”出生于1967年的巴尼在爱达荷州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12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移居纽约成为一名抽象画家,此后,他时常往返于爱达荷州与纽约之间,并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最初的艺术启蒙。

在中学时代,他曾是摔跤和橄榄球运动员,做过时尚模特,接着步入耶鲁大学,先后就读于医学和艺术专业。在耶鲁读本科时期,巴尼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毕业两年后在旧金山现代美术馆举办了第一个个展,并迅速蹿红于国际艺术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短短十余年间,巴尼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当代艺术大展。此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绘画约束》、《奥拓轴》、《悬丝》、《重生之河》等数个系列的30余部影像及相关绘画、雕塑和装置等,其创作力度和制作规模可谓前无来者,很多作品不仅拥有豪华的技术团队,更有各路明星或名人的加盟和出演。在阐述《悬丝》系列时,巴尼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叙事雕塑”的概念,即通过不同媒介的拼接,将各种视觉表达形式融合为一个综合体,从而形成一种“总体艺术作品”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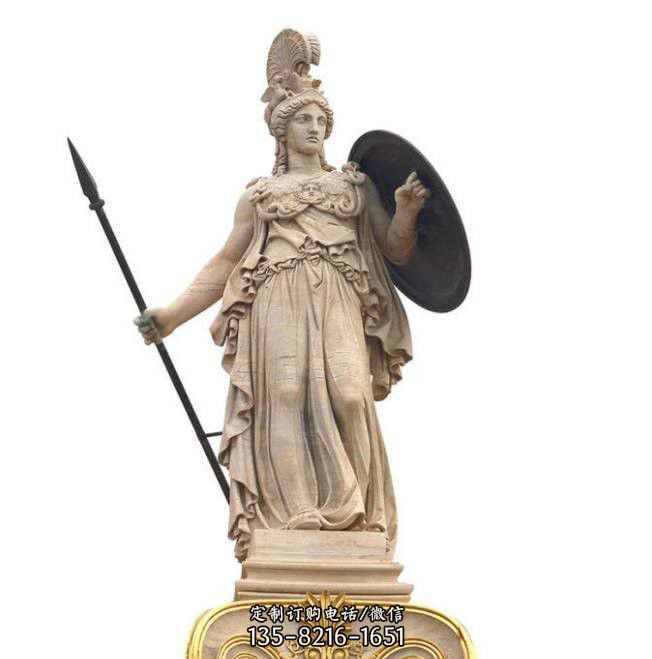
与巴尼以往作品相似,《堡垒》是一件运用摄影、音乐、舞蹈、表演、装置及雕塑等媒介元素创作而成的综合艺术品。在这部作品中,巴尼既是创作者,也是编剧,同时扮演作品中唯一的男性角色。正如丹托所说,马修·巴尼竭力收集当代一切可供利用的艺术资源,以其炼金术般的创作手段加以转化,生产出新的视觉形象。除了对媒介的综合运用,他的作品往往包含对绘画、文学、电影等跨艺术领域的综合杂糅,以及对历史、宗教、神话、科技、体育等复合知识系统的挪用与援引,通过替换、增减或异化的艺术语法对作品结构实现推进、中断、悬置、混杂或抵消。

在这种类似化学反应的创作效应中,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艺术生产的特征。如展览手册中所介绍,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诗集《变形记》中描述的狄安娜与阿克泰翁的故事,是《堡垒》的主要叙事蓝本,也是西方艺术史中常见的图像主题。在罗兰·巴特看来,“神话是一种言语”,一切事物都可以是神话。神话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意指。神话是巴尼创作中惯用的修辞方式,在《堡垒》中除了对《变形记》的挪用,还包含对基督教符号、萨满巫术、占星术等神秘仪轨的援引。其次,影片中几乎每个角色都交叠着多重身份,从而在多重能指的互文之间生成混杂的意指。显然,对于巴尼来说,神话不仅是一种普适性的修辞,更重要的是作为他在建构其混杂的艺术制作中处理时间、空间等各种裂隙的想象工具。

在英文中,一词除了捕猎,还有搜寻、追踪等含义,而在作品中,譬如巴尼所扮演的角色显现出守林人、画师、猎人等多重身份,所有的形象无不指涉着多重的视觉意象。影片开启于黎明时分,翱翔的雄鹰俯瞰着冰原中一团猎物的残骸。白雪覆盖的山林里,女神狄安娜和她的两个侍女从睡梦中醒来。一辆房车内,占星师正在对一幅铜板绘画进行电镀,随后将两块崭新的铜板交给守林人。守林人携带铜板进入山林,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装上一台热感应监控器。

夜晚,守林人从电脑屏幕上看见监视器拍摄到的女神的身影,女神凝视着监视器,守林人凝视着屏幕。房车内,占星师制作了一座由赫拉克勒斯神像顶起的占星装置,并在装置前缓慢舞蹈。第二章,两个侍女在山谷的温泉中沐浴,坐在一旁的狄安娜仔细地擦拭着手中的枪械。守林人再度进入山林,偶遇一只被猎犬围困于树上的美洲狮,他随即在雪地中支起一座射击台,开始在铜板上描绘美洲狮,并将其射杀。山林的另一边,正在寻猎的女神被远处的犬吠声所吸引,转身朝声音的方向走去。

回到营地的房车内,守林人在铜板上画下了女神在雪林中的容貌。第三章,女神蹲守在雪花弥漫的山林中,两个侍女辅助女神架枪瞄准远处山坡上的一匹野狼。另一侧的雪地里,守林人俯靠在射击台上悄悄描绘女神捕猎的场景。女神透过瞄准镜发现了守林人和射击台上的铜板,她扣动扳机,一声枪响,子弹击碎了守林人的枪管,接着划过铜板,在描绘着她举枪射击的镜像画面上灼烧出一片黑影和一记弹痕。第四章,夜晚,守林人窥视着女神的帐篷,试图再次描绘女神及其侍女。
女神忽然携枪冲出帐篷,透过夜视镜,发现了守林人的踪影。她再次扣动扳机,枪声响起,子弹击破了铜板,在描绘着女神野营地场景的画面上射出了一个窟窿。第五章,晴日,守林人驱车来到山脚下的小镇,经过镇上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时,他窥见礼堂内一名印第安女子正在准备用圆圈表演的舞蹈。守林人来到小镇上的酒吧,点了一杯咖啡,坐在吧台前翻开手中的笔记本,开始用笔勾画着一匹狼的头像。
印第安女子开始了她的舞蹈,有节奏地将摆放在地板上的红色圆圈一一拾起套进身体。山林中,女神在一名侍女的辅助下,站在山顶处眺望远方。身后,另一名侍女高悬在一棵粗壮的被山火焚烧过的树干上,手握缆绳如美洲狮一般曲展身体,上下翻舞。最后,守林人合上笔记本离开了吧台,留下一杯一口未喝的咖啡;印第安女子戴着耳机,随着苹果手机里播放的音乐节奏,将缠绕在身体上的十多个红色圆圈不断组合变化。空荡荡的礼堂里,红色的圆圈沿着女子的舞姿如翅膀般上升,在门缝的逆光中,印第安女子化身雄鹰。
攀登树干的侍女最终如一只被击杀的猎物沿着缆绳落下,另一名侍女将其慢慢接住,天色渐暗,夜幕降临。第六章,山林中,女神和两名侍女再次发现野狼,并将其猎杀。随后,她们来到山谷瀑布边,女神从口中向枪管吐出一团蜂蜜般黏稠的液体。被女神猎杀的野狼坠落山谷,听闻枪声的守林人随即赶到,剥下并盗取了狼皮。朝霞从山林深处升起,占星师走出房车仰望天空,在河边开始舞蹈。群狼拥入房车内,狂欢般地撕咬破坏着人类居所内的一切设施。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犬吠和狼啸,天空中出现日全食,天地渐渐昏暗混沌。朝霞与黑夜,追踪与隐藏,进攻与防守,压抑与释放等对立的意象,往复于影片的六个段落中——恰如丹托所述,“上升与下降的诗学”是巴尼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张力。军事要塞,退避的心理状态,意识形态的隔离,以及近十年在巴尼的故乡周边兴起的名为“美国堡垒”的政治运动。在西方殖民史中,堡垒作为一种防御工事,也象征着征服。
与地理大发现前后并行的文艺复兴不仅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也引领了影响深远的军事革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者格欧菲瑞·帕克指出,15世纪末,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意大利的建筑工艺迅猛发展,一座座教堂耸立的同时,以星形堡垒为代表的军事工事也改变着战争状态,进而导致了欧洲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变革,为西方的全球霸权铺平了道路。在另一本名为的书中,作者瑞勒·加特兰德详尽描述了16世纪至19世纪的数百年间,被各式各样的堡垒所包裹庇护的驿站和城镇是如何自北美东海岸的港口一直延伸向广阔的西部荒原的。
影片第五章中,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礼堂跳圈舞的印第安女子,恰似一只被殖民者的堡垒侵占了巢穴又被禁锢于堡垒之中的雄鹰,历史与文明的阴影纠缠在舞者无人观看的表演中。人类即将陷入技术文明的全面崩溃之中,所有的大城市都将处于这场灾难的风暴中心,混乱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人裹挟。而逃生的唯一方法,便是在这场大灾难来临之前远离城市,逃到广袤的森林地区,在那里建立人类文明最后的堡垒。这场运动不仅煽动着美国部分保守主义者向爱达荷州等西部边疆迁徙的地缘政治活动,更激发了经济层面和宗教层面的物质与精神想象。
运动的倡导者要求人们在迁徙中变卖所有家当,同时制定一份堡垒生活清单,储备枪支、皮卡、船只、药品、粮食、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土地等。除此以外,在堡垒区域生活的人应当主动逃离现代货币系统,恢复以物易物的经济方式和耕种打猎等传统经济劳作,以邻里关系为结构,建立基于基督教原教旨信仰的教会组织。而在19世纪初南北战争之后,受林肯推崇的爱默生思想,即倡导所谓“大地意识”的超验主义与自然主义,成为了美国文明精神的核心。
从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直至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诺曼·梅勒的《古老的夜晚》,自然与技术之争的思想博弈从激进到保守,始终徘徊于美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军事堡垒到文化堡垒,再到精神堡垒,巴尼围绕其故土的锯齿山脉勾勒的,是一幅矛盾而复杂的美国精神文明的变迁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在展厅深处的两件装置作品——《射击台上的狄安娜》和名为《堡垒》的祭坛画龛——或许可以被视为巴尼对整个展览的形象化总结:
女神的画像取代了枪支,被安放在镀金的射击台上,而祭坛画龛内的圣像画被扭曲的电镀风景所取代。回到影片中的叙述,不难发现两件装置的生成与“堡垒”主题之间的联系。巴尼扮演的守林人,一方面以在铜板上描摹勾勒图像的技术主义方式记录和研究自然,在此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女神的行踪,并试图以同样的技术方式捕捉并再现女神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猎人的他在记录与研究自然的同时,也不断试图征服和占有自然。
在此过程中,作为山林的主宰、代表自然秩序的女神一次又一次地对守林人的行为发出警告:在此之后,守林人盗取了女神的猎物,同时,日食的发生使得天地一片混沌黑暗,自然的力量最终毁灭了人类用技术创造的栖居之地。守林人的身份在射击台这一悖论装置前发生分裂,影片中射击台既是猎人的武器的辅助设施,也是画师户外写生的画架。射击与摄影无疑具有着多重同构性,桑塔格和维利里奥都曾详细说明过摄影术的发展与战争技术发展的密切联系。
所以在此处,射击台上的枪和画板的并置与其说是技术形式的对比,不如将其视为新旧媒介的对立。与传统媒介相比,摄影或许更依赖于非自然的技术工具,从而始终处于某种人工与自然的内在矛盾当中,对这种矛盾的展现及克服行为即为影像。在这两件作品中,守林人孜孜以求的形象——女神的画像取代了他的终极技术工具——枪,原本安放着圣像的祭坛画龛被经过技术锻造的自然风景所占据,看上去仿佛两座矛盾而空洞的形象的堡垒。显然,这两件从影像中生产的装置作品不是展览的句号,更像是历经末日后的遗存,或许透露着点滴残缺而叵测的启示?丹托认为马修·巴尼的艺术“体现了我们时代中所独有的思虑”,或许可以把这样的思虑视为米歇尔针对当代视觉表征定义的“焦虑”。
在无机的拟像中,形象不仅是具有生命的有机组织,更是有欲望的事物。形象本能地需要介入,寻求探讨形象与观念、形象与观众及形象之间的联系。我们无法确定在《堡垒》所呈现的诸多形象中,是否蕴含着“野火烧不尽”的生生不息,但当置身于本土的视角,去观看巴尼的故土——遥远的爱达荷风景时,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对自然真理的敬畏,与对技术生命的渴求,两者不断往复于人类文明的矛盾张力之中。
在这个影像泛滥的时代,值得我们反思或质疑的是,如何平衡我们生活的堡垒与我们生存的自然风景?或许,这也是那些通过影像而构建的乌托邦,为我们最终带来的面对未来的共同愿景。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