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衣贴体,衣纹厚重有力,躯干正面和后背衣纹呈“U”形。背光及台座早年失落,仅存像身部分,鎏金局部尚有遗存。佛发为高肉髻,上有浅线刻发纹,仍属4~5世纪佛像普遍流行的所谓磨光式肉髻。佛像左手抓大衣一角,右手施无畏印,整体动态和框架有着犍陀罗佛像整体构图的影响,特别是大衣边缘下垂至膝部的形式,可看出这种表现方法的一致性。通观4~5世纪的佛坐像,佛发髻以所谓磨光肉髻的形式占绝大多数,即佛发正中肉髻不刻划发纹,有如一颗大圆珠,圆润光亮,极为醒目。

这种磨光肉髻形式应是4世纪十六国时期至北魏初期佛像的一般规律,为当时的流行样式,也是判断佛像时代的着眼点之一,一直到北魏依然流行,如云冈20窟大佛高达17米,堪称雄伟,也是磨光肉髻。法常造释迦佛像前胸上刻摩尼宝珠及火焰纹,纹饰细腻,线刻流畅,早期佛像上出现这种纹饰很少见。在佛像胸前出现的摩尼宝珠及火焰纹可见龙门石窟北魏开凿的古阳洞北壁第234龛陆浑县功曹魏灵藏等造像,此像是太和末至景明年间所造。禅定佛像双手作禅定印,袒右肩大衣,结跏趺坐,胸前浮雕有火焰宝珠纹,宝珠中心有一“卍”字。

又在南壁第66龛比丘法生造像,是景明四年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所造像龛的主佛也是禅定坐佛,胸前也有同样的宝珠纹,正中心位置也可见“卍”字。这二尊像都是北魏时期佛像上出现摩尼宝珠及火焰纹,较为少见。法常造佛像可以说是目前所见在佛像胸前最早出现的摩尼宝珠及火焰纹。法常像的制作时代,其造型框架和细部手法与同时代石窟造像和独尊铜佛像相比较,直观判断,应该是4世纪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如原日本新田氏收藏的禅定佛坐像,高15.2厘米,及多尊4世纪的小型铜佛像,可以大致判断时代。

这类小型金铜佛像至今所遗较多,中外各博物馆多可见到,绝大多数是禅定佛坐像,背光和台座已失落,仅存佛身,站立像几乎看不到。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尊金铜佛立像,高15.5厘米,时代较法常像似乎略晚。法常,《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恰有佛图澄的弟子名法常。适逢永嘉之乱,先隐居草野,后投奔石勒,深得石勒及侄石虎的崇信。文中记有,佛图澄止于邺城内中寺,派弟子法常北上襄国。法常与从襄国而来的弟子法佐相遇,二人在城墙下共宿,谈话议及师父,神僧佛图澄全都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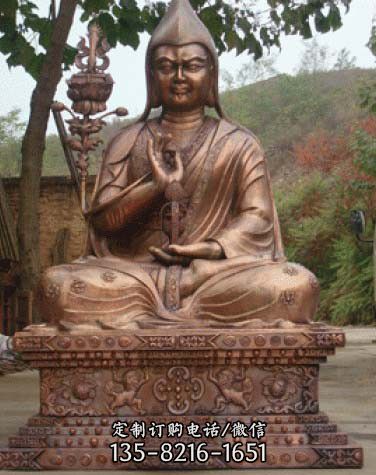
僧人法名虽然难免重复,但这尊佛像与“佛图澄传”的法常名字相符,与佛图澄当年活动的后赵地域都能吻合,推断这尊金铜佛像背后所刻的后赵和僧人名字就是佛图澄的弟子法常。因此,法常像的制作年代应该在320年至351年之间。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是在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匈奴、羯、羌、鲜卑等少数民族一时间纷纷独立建立的小朝廷,有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和夏,共十六国。从304年刘渊称王,一直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为止,前后共135年。

活动疆域也多在今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北一带,即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虽有陆路与海路之分,但主流上,佛教是循着丝绸之路而进入内地的。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往往多崇信佛教,西域的高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都曾被后赵的石勒、石虎叔侄和后秦的首领姚兴所迎请,礼遇甚高。前秦、北凉的上层统治者也都曾凿窟建寺、塑造佛像,至今十六国时期的石窟在敦煌、金塔寺、天梯山、文殊山、炳灵寺等都有遗存。

特别是十六国时期的小铜佛像也仍有不少传世品和出土品。这些佛像由于绝大多数没有铭文,所以,到底是十六国时代哪个王朝铸造的很难确指,但它们的造型规律还是一致的。石勒于319年称赵王,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建都襄国,后迁都到邺。石勒、石虎叔侄都笃信佛教,隆重迎请龟兹高僧佛图澄。据《邺中记》,石虎造金佛像,坐于檀车,九龙吐水灌之,极尽一时之盛。

以至于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路过中山,对那里的佛教盛况留下深刻印象。十六国时期虽然被认为是乱世,但却是西域和河西走廊与中原佛教密切交流的时代。佛教艺术传入西北印度,然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丰富了汉魏以来的传统画塑技法,形成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风格。尽管法常僧的资料极为贫乏,但在高僧佛图澄的活动之地能够发现法常刻款的金铜佛像,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此像有可能就是佛图澄的弟子法常发愿制作的,若如此,将为研究佛图澄的事迹增添了一点宝贵的实物资料。

法常造金铜佛立像能够出现在有着深厚佛教背景的后赵地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在佛教艺术史上,带有铭文的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所见甚稀,凤毛麟角。首屈一指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金铜佛像当属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后赵建武四年比丘竺某造金铜佛坐像,高39.7厘米。该像为高肉髻,束发状的佛发,宽额,大眼横长,身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形式为图案化的“U”形,等距离分布于胸前和前襟部,衣纹断面是浅阶梯形的,双手重叠于胸前作禅定印,趺坐在四方台座上。

正面有三孔均匀分布,结合其他佛像分析,这位置两侧原来应该嵌有两头浮雕的狮子,中间部分当年应嵌有水瓶花叶或者是汉式的博山炉。重要的是背后残留有铭文∶“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旧例,魏晋时僧人的法名前冠以“竺”,表示他的籍贯是印度;据此也可以推知,后赵国当年崇信外国僧人,曾经邀请了印度和西域等地多名外来僧人。此像的形式和建武四年坐像大同小异,只不过佛像下铸4足,与像身连为一体。这种做法早期较为少见,十六国的佛像绝大多数是佛像身躯部分和4足是分别铸造的,然后套接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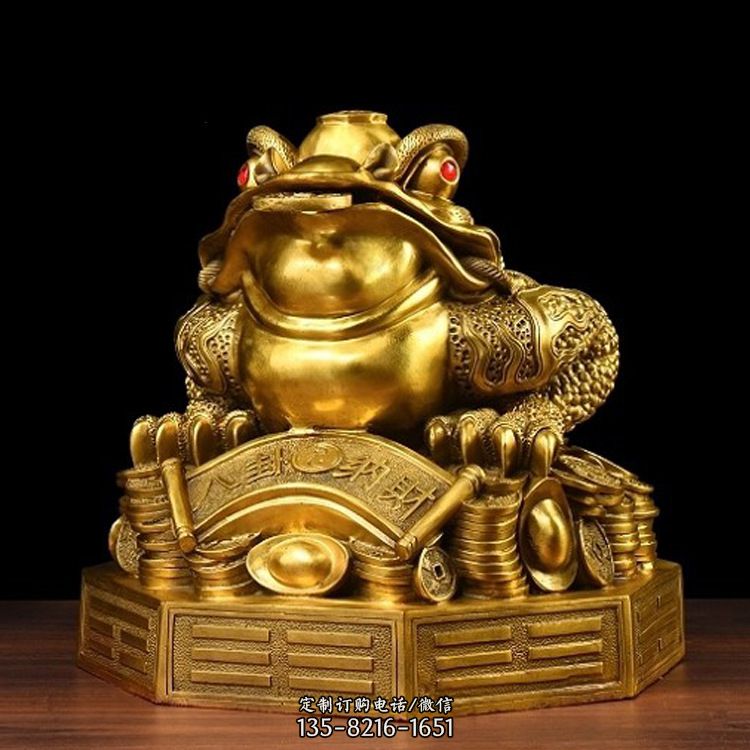
这尊佛像的4足表面上刻有发愿文∶“胜光二年已巳春正月朔日中书舍人施文为合家平安造像一区。”据发愿文可知,此像是匈奴赫连夏胜光二年中书舍人施文出资铸造的。407年匈奴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建都统万城,418年一度夺取长安即称帝,431年为吐谷浑所灭,此像是灭国前二年所造。上述二像均有铭文,为我们判断这类金铜佛像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具有重要的标尺作用。值得注意的还有1979年西安文管会从废铜中收购的一尊金铜禅定佛像,磨光肉髻,通肩大衣,衣纹在肩部断面呈起伏阶梯形,立体感颇强。
像背后刻有佉罗文,据林梅村先生考证,意为“此佛为智猛所赠,谨向摩列迦之后裔,弗斯陀迦·慧悦致意”。他认为铭文的特点应是4世纪末,弗斯陀迦·慧悦应是大月氏望族摩迦列的后裔。佉罗文起源于犍陀罗地区,2~4世纪流行于中亚,4世纪后渐废,在于阗、疏勒、龟兹及敦煌汉长城遗址中都有发现。内地则在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发现过一处佉罗文井栏题记。而长安发现的这尊佛像的大磨光肉髻、面相有些类似汉族,大衣前的坐垫为汉代流行的菱格纹和三角纹,从诸方面风格分析,此像是制作于中亚至长安一带的,铸造者可能是汉化了的大月氏人。1955年河北省石家庄北宋村出土了一尊铜佛像,高19厘米,全体由佛身、背光、圆伞盖和4足方座共4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都是可以拆卸组装的。
背光上铸有二供养人、二飞天,正上方佛像头部又有一小坐佛,当是象征着身居兜率天宫的弥勒佛,在伞盖边缘还残留着垂饰物。甘肃泾川县玉都乡也出土过一件同类型的佛像,高19厘米,构造与石家庄北宋村佛像大同小异,佛像的背光为身背光和头背光二重组合式,上方为圆形天盖,盖顶亦饰有莲瓣纹。从上述两件完整佛像可看到,目前存世的十六国佛像多数是当年配有背光、伞盖、台座等完整佛像的一部分,由于分铸套接,时代久远,故配件多已散失了。
1988年,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曾举办“中国古式金铜佛和中亚及东南亚的金铜佛展”,内中十六国铜佛共出展40余尊,全部是佛身部分,仅有二、三尊还套有4足方座。这些佛像脑后均有榫,可知当时应有背光,又底部全部为中空,平面呈凹形或四方形,推测当年下部应套接于4足方座上。建武四年像和大夏胜光二年像均为束发形的高肉髻,发纹清晰深刻,但通观此时期佛坐像,佛发髻以所谓磨光肉髻的形式占绝大多数。这种磨光肉髻形式应是十六国佛像的一般规律,是当时的流行样式。十六国时期北方盛行坐禅,这种小像是禅观的对象或是祈福禳灾的供养佛像,而立像很少,一般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巡行说法的形式,称为“经行像”。
前述的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金铜佛立像,头部为磨光肉髻、蓄髭、通肩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衣角,整体造型似乎仍残留犍陀罗佛立像框架,台座上刻“造佛九躯”数字。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的4世纪金铜菩萨立像,高32.9厘米,一般认为是弥勒菩萨,菩萨左手持水瓶,帔帛搭于左腕的下方,帔帛下方呈多曲的折带纹。右侧衣褶底部褶皱作成3个菱弧形,这组衣褶在此种衣纹可以溯源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的表现衣纹的雕刻上,在犍陀罗的雕刻上也可以见到此种形式。可以说,十六国的佛像有着通过西北印度和中亚地区带来的地中海的某些造型因素。
十六国的佛像可说是我国公认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单尊铜佛像,虽然在此之前东汉的墓室墓葬中已出现了早期佛像,如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的陶钱树座上已有一佛二供养人的佛雕像,又四川麻浩汉墓横梁上也浮雕有佛坐像,但那时是基于什么理论将佛像安置在墓葬中尚可探讨。作为单尊的以礼拜供养为目的的佛像似应以十六国佛像为始。法常造像可以说是在我们已知的仅有的数尊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的基础上又新发现的此时期的金铜佛像,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