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秉明,云南人,生于南京,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之子,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之后转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旅法期间的艺术创作,以雕刻为主,但对绘画、书法、文学也有涉猎,曾以一系列动物主题的铁焊作品及石膏水牛题材作品闻名。1962年起执教于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曾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同时从事书法实践与教学研究,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1989年退休。

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展览会的观念》《回归的雕塑》《看蒙娜丽莎看》《张旭与狂草》等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去拜访当时已有名气的雕刻家艾坚·玛尔丹。辛亥革命以来,“五四”以来,年轻的中国人有几个读过《老子》?而在西方文化环境中,这五千言的小书发射着巨大的光芒。一九六四年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汉学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老子》的报告,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谈“无为”。

对佛教雕刻也一样,在中国关心佛教雕刻的年轻人大概极少。我初到欧洲,看见古董商店橱窗里摆着佛像或截断的佛头,不但不想走近去看,并且很生反感,觉得那是中国恶劣奸商和西方冒险家串通盗运来的古物,为了满足西方一些富豪的好奇心和占有欲,至于这些锈铜残石的真正价值实在很可怀疑。这一年的1月31日我和同学随巴黎大学美学教授巴叶先生去访问雕刻家纪蒙。到了纪蒙工作室,才知道他不但是雕刻家,而且是一个大鉴赏家和热狂的收藏家。

玻璃橱里、木架上陈列着大大小小的埃及、希腊、巴比伦、欧洲中世纪…那是我不能忘却的一次访问,因为我受到了猛烈的一记棒喝。把这些古代神像从寺庙里、石窟里窃取出来,必是一种亵渎;又把不同宗教的诸神陈列在一起,大概是又一重亵渎,但是我们把它们放入艺术的殿堂,放在马尔荷所谓“想象的美术馆”中,我们以另一种眼光去凝视、去歌颂,我们得到另一种大觉大悟,我们懂得了什么是雕刻,什么是雕刻的极峰。在这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确曾嘲笑过所谓“国粹”,但是我不再这样想了。

不,我以为我走前一步了,我跨过了“当务之急”,而关心较长远的事物。后来我读到瑞典汉学家喜龙仁的《五世纪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我于是更明白西方人在佛像中看见了什么。有时好像浸在不可测度的沉思中,无论外部的表情如何,人们都可以看出静穆与内在的和谐。拿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和某些中国佛像、罗汉像作比较,例如试把龙门大佛放在摩西的旁边,一边是变化复杂的坐姿,突起的肌肉,强调动态和奋力的戏剧性的衣褶;

一边是全然的休憩,纯粹的正向,两腿交叉,两臂贴身下垂。衣纹恬静的节奏,和划过宽阔的前胸的长长的弧线,更增强了整体平静的和谐。请注意,外衣虽然蔽及全身,但体魄的伟岸,四肢的形象,仍然能够充分表现出来。严格地说,衣服本身并无意义,其作用乃在透露内在的心态和人物的身份。几乎没有个性,也不显示任何用力、任何欲求,这面容所流露的某一种情绪融注于整体的大和谐中。任何人看到这雕像,即使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也会懂得它具有宗教内容。

这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在鼓动着,并且感染给观者。这样的作品使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的雕刻虽然把个性的刻画推得那么远,其实那只不过是生命渊泽之上一些浮面的漪澜。显然,在喜氏这样一个西方鉴赏家的眼睛里,佛雕是比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更高一层次的作品。他看佛像一如我们看《摩西》,我们同样渴求另一个文化的特点来补足自己的缺陷。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倾慕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由于我们的时代处境需要一种在生存竞争中鼓舞战斗精神的阳刚的艺术。我们要像摩西那样充满活力,扭动身躯站起来,要像《行走的人》那样大阔步迈向前去,我们再不能忍受趺坐低眉的典雅与微笑。

喜氏相反,从中世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惨烈的形象起,甚至更早,从希腊神殿上雕着的战斗的场面起,西方人已描绘了太多的世间的血污与泪水,恐惧与残暴,一旦看到佛的恬静庄严,圆融自在,仿佛在沙漠上遇到绿洲,饮到了甘泉。我完全折服于他对古今雕刻评鉴的眼力,我想,在这样锐利、严格、高明的眼光下受锻炼是幸运的。纪蒙指导学生观察模特儿的方法和一般学院派很不一样,从出发点便有了分歧了。他教学生把模特儿看作一个造形结构,一个有节奏,有均衡,组织精密,受光与影,占三度空间的造形体。

按这原则做去,做写实的风格也好,做理想主义的风格也好,做非洲黑人面具也好,做阿波罗也好,做佛陀也好,都可以完成坚实卓立的作品。所以他的教授法极其严格,计较于毫厘,却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对罗丹极为推崇,而他的风格和罗丹的迥然不同,罗丹的作品表面上留着泥团指痕;他说看罗丹的作品,不要错认为那是即兴的捏塑,我们必须看到面与面的结构和深层的间架,这是雕刻的本质。雕刻之所以成为雕刻,在佛像中,他也同样以这标准来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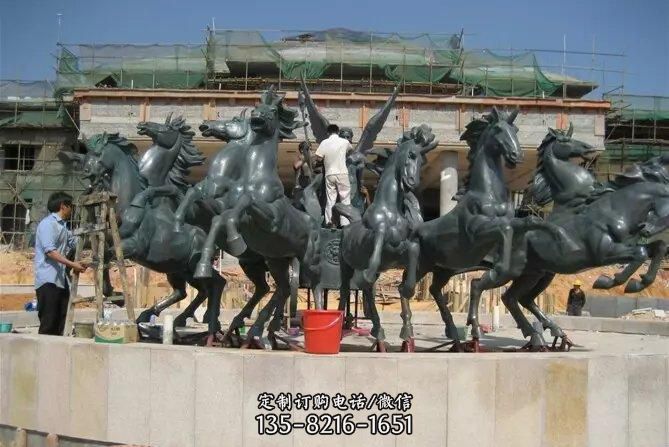
有的佛像只是因袭陈规茫然制作,对于空间,对于实体,对于光影,对于质地毫无感觉,在他看来根本算不得雕刻。当然罗丹的雨果、巴尔扎克和佛像反映两个大不相同的精神世界。佛像相反,表现涤荡人间种种烦恼后,彻悟的澄然寂然,但是从凿打捏塑创造的角度看,它们属于同一品类,凭借同一种表达语言,同样达到表现的极致。我逐渐明白,我虽然不学塑佛像,但是佛像为我启示了雕刻的最高境界,同时启示了制作技艺的基本法则。

我走着不同道路,但是最后必须把形体锤炼到佛像所具有的精粹、高明、凝聚、坚实。第一步要排除宗教成见,无论是宗教信徒的成见,还是敌视宗教者的成见。对于一个笃信的佛教徒而言,他千里朝香,迈进佛堂,在香烟缭绕中感激匍匐,我们很难想象他可以从虔诚礼拜的情绪中抽身出来,欣赏佛像的芝术价值。对于一个反宗教者来说,宗教是迷惑人民的“鸦片”,佛像相当于烟枪筒上银质的雕花,并不值得一顾的。
同样地,一个反宗教者当然也很难把蔑视、甚至敌视的对象转化为欣赏的对象。所以要欣赏佛像我们必须忘掉与宗教牵连的许多偏见与联想,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要把佛像从宗教的庙堂里窃取出来,放入艺术的庙堂里去。一二百年前西方油绘刚传到中国,中国人看不惯光影的效果,看见肖像画的人物半个脸黑,半个脸白,觉得怪诞,认为丑陋。后来矫枉过正,又把传统中国肖像看为平扁,指斥为不合科学,并且基于粗浅的进化论,认为凡非写实的制作都是未成熟的低阶段的产物。
到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传来,狭隘的写实主义观念才又被打破,中国古代绘画所创造的意境重新被肯定。京剧也同样,一度被视为封建落后的艺术形式,西方现代戏剧出现,作为象征艺术的京剧价值重新被认识。因为我们有一个欣赏京剧的传统,却并没有一个欣赏佛像的传统。关于讨论绘画的艺术价值,我们有大量的画论、画品、画谱,议论“气韵”“意境”“风神”“氤氲”…对于雕刻,评者似乎只有“栩栩如生”“活泼生动”“呼之欲出”“有血有肉”一类的描写,显然这是以像不像真人的写实观点去衡量佛像,与佛像的真精神、真价值全不相干,我们必须承认北魏的雕像带石质感,有一定的稚拙意味,如果用“栩栩如生”来描写,那么对罗丹的作品该如何描述呢?
如果用“有血有肉”来描写,那么对17世纪意大利雕刻家贝尼尼的人体又该如何描述呢?第三步,我们虽然在前面排斥宗教成见,却不能忘记这究竟是一尊佛。“佛”是它的内容,这是最广义的神的观念的具体化,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宗教和形而上学去。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佛”的观念在人类心理上的意义,不能领会超越生死烦恼的一种终极的追求,那么我们仍然无法欣赏佛像。如果“生动”是指肌肤的摹仿,情感的表露,那么,佛像不但不求生动,而且正是要远离这些。佛像要在人的形象中扫除其人间性,而表现不生不灭、圆满自足的佛性。
无论外界如何变幻无常,此主体坚定如真金,“道通百劫而弥固”。要在佛像里寻找肉的颤栗,情的激动,那就像要在18世纪法国宫廷画家布舍的肉色鲜丽的浴女画里读出佛法或者基督教义来,真所谓缘木求鱼。佛像的内容既然是佛性,要表现这个内容定然不是写实手法所能承担的。找一个真实的人物来做模特儿,忠实地摹仿,至多可以塑出一个罗汉。佛性含摄人间性之上的大秩序,只有通过一个大的造形秩序才能体现,所以要欣赏佛像必须懂得什么是造形秩序。从婴儿到成人,我们一点一点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以及主观世界的规律,学会服从规律,进而掌握规律,进而创定新秩序。
因为所提的问题不同,回答的方式不同,于是有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分野。凡佛经所讲的五蕴、三界、四谛、十二因缘、八识、圆融三谛,等等种种,都不外是对内外宇宙所说的有秩序的构成,对此构成有贯通无碍的了识便成悟道。佛像艺术乃是用一个具体形象托出此井然明朗的精神世界,以一个微妙的造型世界之美印证一个正觉哲思世界之真;在我们以视觉观赏此造形秩序的时候,我们的知性也似乎昭然认知到此哲思秩序的广大周遍;一如灵山法会上的拈花一笑,造形秩序的一瞥,足以涤除一切语言思辨,直探形而上的究竟奥义。
佛的形象虽然从人的形象转化而来,但人的面貌经过锤铸,升华,观念化,变成知性的秩序,眉额已不似眉额,鼻准已不似鼻准…每一个面的回转都有饱满的表面张力,每一条线的游走顿挫都含几何比例的节奏…其整体形成一座巍然完美和谐的营造,打动我们的心灵。建筑物并不摹仿任何自然物,它只是一个几何结构的立体,然而它的线与面在三度空间中幻化出庄严与肃穆;它是抽象的,然而这些线与面组构成一个符号,蕴涵一种意义,包含一个天地,给我们以惊喜、震慑、慰抚,引我们俯仰徘徊。
懂得了这一点,然后可以步入殿内,领略含咀佛像所传达的消息。中国两千年来,因文人艺术观的影响,雕塑被视为劳力的工匠技艺,被排斥于欣赏对象之外。西方艺术史家为我们提醒了佛教雕刻的价值之后,我们又把它归入封建意识的产物,仍然未能深入地去研究,去发掘,去欣赏。过去把文化问题一概放到历史进程的框架中去观察解说,认为中国文化是封建的,中古的,该被淘汰的。经过长期片面的自我否定后,发现问题并不那么单纯,终于开始容纳不同的理论,逐渐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西。并认识到中国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把过去带着强烈偏见加以抹杀的传统重新作估价。
西方人如喜龙仁等,在看到佛像的时候,仿佛看到一片新天地,跳跃欢喜。我们今天带着新的眼光回头来看佛像,应会有比喜氏更复杂的心情。那是对自己古传统新的正视、新的认同、新的反思,而有久别回归的激动吧。部分文章收集整理于网络,推送时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png)
















 微信/电话同号
微信/电话同号